蔣復璁著《珍帚齋文集》補正
張錦郎 國家圖書館編纂退休
【摘要】《珍帚齋文集》係蔣復璁先生六十年來的著作選集,分為五卷。全書2,130頁。本文主要對卷二進行校勘、箋注及述評,其中多與中央圖書館史實有關,如陷區購書等,卷一、五只校正部分文字,卷三、四因專業不足,未敢評注。文末兼及本文集編輯方法的探討,如宜附大事年表、著作目錄及書後索引等。
關鍵詞:蔣復璁;中央圖書館;戰時陷區購書;中國圖書館事業;故宮博物院
前言
蔣復璁先生曾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故宮博物院院長。《珍帚齋文集》係蔣先生六十年來的著作選集,收三百二十餘筆,以單篇論述文字居多,序文次之,專書兩種。按內容分為五卷,卷一為文化、藝術、博物館;卷二為圖書與圖書館;卷三為宋史與歷史類;卷四為宗教;卷五為雜論,多蔣先生悼念師友之作,凡不屬上述四類者,歸入此類。正文前有錢穆、張其昀、昌彼得序文各一篇,及自序一篇。全書2,130頁,卷二圖書與圖書館幾近千頁。本文主要對卷二進行校勘、箋注及述評,其中多與中央圖書館史實有關,如陷區購書等,卷一、五只校正部分文字,卷三、四因專業不足,未敢評注。文末兼及本文集編輯方法的探討,如宜附大事年表、著作目錄及書後索引等。
〔卷一:文化、藝術、博物館〕補正
卷一頁9,自序第三段「民國十五年,中華文化基金董事會創立北京圖書館,亦即國立北平圖書館之前身」。有兩個地方待商榷:
| 1. | 1924年5月21日美國國會通過將退還庚款用以發展中國教育文化事業。同年9月中美雙方會同組織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珍帚齋文集》(以下簡稱《文集》)卷二頁568,寫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卷二頁621、883寫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卷五頁47,也寫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卷二頁569,寫成中華文化基金董事會,《蔣復璁口述回憶錄》頁102-103都寫成中國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以上四種名稱都錯了。王振鵠老師在《蔣復璁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頁34,寫成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中國大陸出版的《中國現代社團辭典(1919-1949)》頁197,也寫成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也都錯了。 |
| 2. | 說北京圖書館是國立北平圖書館的前身,小部分講對了。這是圖書館史上的大事,不能不說清楚。國立北平圖書館的前身是京師圖書館,民國元年8月開館售券(事實上民前3年7月學部就奏設京師圖書館),民國15年教育部提出閣議,將京師圖書館改組為國立京師圖書館,民國17年改稱國立北平圖書館。北京圖書館成立於民國15年,17年易名北平北海圖書館,民國18年國立北平圖書館與北平北海圖書館合組。為了進一步釐清京師圖書館、國立京師圖書館、新舊國立北平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北平北海圖書館(或北海圖書館)六所圖書館的關係,筆者特製表如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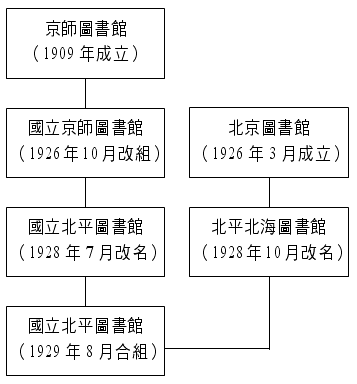
卷一頁157,《文集》載:「三、出版物方面:定期刊物,有故宮月刊、故宮週刊、故宮書畫集、史料旬刊等;單行本的刊物,法書、名畫、影印圖書各有四十餘種,文獻刊物也有三十餘種。」有二誤:
| 1. | 過去「刊物」泛指印刷出版品,現在有廣狹二義:廣義指期刊和報紙;狹義單指期刊,不論定期或不定期,即連續出版品。《文集》所列《故宮月刊》、《故宮週刊》、《史料旬刊》是屬於刊物。《故宮書畫集》屬美術類圖書,是書畫冊,雖然形式上隔一或二月出版一期(共出四十四輯),仍非期刊。 |
| 2. | 「單行本的刊物」是不通的名詞。單行本,通常指「不編入著作集,單獨印行或發行的單篇著作」、「從套書中選出具有獨立性的部分,單獨編頁碼,以單冊形式印行的出版物」、「在報刊上連載,然後彙集在一起,以單冊形式出版的作品」。《文集》所指法書、名畫影印最多,不下數十百種,或為立軸、單張、冊頁、明信片式套裝等,不能算是單行本,也非期刊,更不是「單行本的刊物」。至於《文集》所載「文獻刊物也有三十餘種」,似無可能,疑為出了三十二期的《文獻叢編》,其前身是《掌故叢編》,出版十輯。 |
卷一頁162、163,又載:「我們刊印了幾部專門性的刊物」,如《故宮名畫三百種》、《故宮法書》、《故宮藏瓷》。又載:「其他綜合性的刊物」,如《中國文物集成》、《中國文物圖說》,及各種複製畫片、明信片等。上列5種美術圖錄、畫冊和圖說,正如《文集》所說「選材慎重,印刷精良」,有些是民國43至48年之間,由教育部中華叢書委員會出版。另有3種文物目錄,也可略帶一筆,即:《故宮書畫錄》、《故宮銅器圖錄》、《故宮瓷器錄》。以上8種出版品,都可以在《故宮七十星霜》頁184-187找到內容介紹。看完內容介紹,就會認為這些書非專門性和綜合性刊物。
卷一頁157-158,《文集》略謂:民國20年九一八事變後,自民國22年2月6日至5月10日,故宮博物院和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國子監的古物,共19,557箱,從北平南運上海,繼遷南京。其中故宮部分是13,491箱。《文集》卷一頁243,有不同的說法,說故宮部分是13,484箱,與頁158的說法少7箱,所以總數是19,550箱。《故宮七十星霜》頁92,同卷一頁158的說法。
筆者的感覺,卷一除〈故宮博物院院史〉乙文外,較少發生各種疏誤,尤其是統計數字,與《故宮七十星霜》乙書詳加比對,甚少失誤。不像卷二圖書與圖書館部分,連刊名、卷期都錯,更不用說年月日,而且幾乎很少看到有統計數字。
卷一頁159-160,《文集》略謂:民國26年,因抗日戰爭,故宮文物又要向後方遷運。共分三路搶運,《文集》只寫各路裝運的箱數,未寫共多少箱,經筆者退休前在國家圖書館工作統計,共有16,738箱,此與《文集》卷一頁243所載16,650箱,相差88箱。《文集》只寫三路到達的目的地,未寫三路各自出發的時間和到達目的地的時間。不如《故宮七十星霜》乙書用十二頁的篇幅來記錄這一段國寶西遷史。前揭書還特別指出:分三批搶運西遷文物的箱數,各家(如那志良、李濟、劉北氾)記載並不一致。
頁160載:「文物在後方,分存安順、樂山、峨嵋三處,從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到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安靜地保管了八年。」事實上,只有六年多。如果說第二路於民國27年5月22日抵達重慶,也算是目的地,則有七年。重慶於28年5月遭日機瘋狂轟炸,文物9月又由重慶搬往樂山,真正安靜地保管了六年。
卷一頁161,《文集》載:「三十八年七月,成立『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持相同看法的還有杭立武編著《中華文物播遷記》(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乙書所載:「我(杭立武)七月(民國三十八年)再來臺灣,正式成立這一項機構(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按該名稱6月3日的行政院會議就通過。正式成立日期是8月31日。(見前揭書頁39、40)昌彼得總主編《故宮七十星霜》(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乙書頁159,同杭先生的看法。他們的說法都有公文為依據。下列三種說法是錯的:
| 1. | 《文集》卷一頁246,載:「教育部於三十八年一月成立『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與卷一頁161的說法是自相矛盾的。 |
| 2. | 黃克武編撰《蔣復璁口述回憶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2000年)乙書頁69,載:民國37年成立「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則是很離譜的事。 |
| 3. | 《第三次中國教育年鑑》頁826說38年10月間提經行政院會議決定將各機關合併而成立「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則是太晚的說法。 |
頁161接著又載:「四十四年(一九五五)把這個組織改名為『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缺月份。頁191寫成44年1月,頁246寫成44年11月,後者是正確的,杭立武、昌彼得兩先生持相同的看法。
卷一頁162,《文集》載:「民國五十年(一九六一)春,我國政府應美國之請,在美國五大城市舉行中國古藝術品的展覽,運去的文物有九類,共計二五三件。這五個大城市──華盛頓、紐約、波士頓、芝加哥、舊金山──的展覽,是從民國五十年(一九六一)五月二十七日起,到五十一年(一九六二)七月十七日結束,參觀人數達四六五、三四三人。」
依文章順序,分成三點,列舉李霖燦、昌彼得等人不同(或相同)的看法。
1. 參展文物件數
| (1) | 頁162載共計253件,頁172載二百四十餘件。 |
| (2) | 李霖燦著《國寶赴美展覽日記》(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乙書附錄「赴美展覽國寶簡明目錄」編號,共二百三十一號。 |
| (3) | 昌彼得總主編《故宮七十星霜》乙書載:一共253件,其中故宮藏的214件,中央博物院藏的39件。 |
2. 展出時間
| (1) | 頁162載:民國50年5月27日起,到51年7月17日結束。頁172載:「一九六○至一九六一年在美國的展覽也轟動了世界」,誤為民國49至50年。 |
| (2) | 李霖燦前揭書載:始自民國50年5月28日,至51年6月17日止,共三十四週。 |
| (3) | 昌彼得前揭書載:50年5月28日至51年6月17日,同李霖燦說法。昌先生書上寫「總計五地一共展出了二百五十三天」。 |
3. 參觀人數
| (1) | 頁162載:465,343人。 |
| (2) | 李霖燦前揭書載:465,243人,與《文集》所載相差100人。李先生有各地參觀人數的統計,如華盛頓最多,有144,358人;芝加哥最少,有59,674人。不過展出時間不同,華盛頓展出時間有十星期,其餘四地均為六星期。 |
| (3) | 昌彼得前揭書載:四十六萬五千多人。 |
| (4) | 杭立武前揭書未載五地參觀總人數,只列舉華盛頓與舊金山兩地參觀人數,及每日平均為2,255人。 |
卷一頁162,《文集》又載:「兩院(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認為沒有一個陳列室,公開展覽出來,是太不方便了。兩院的經費有限,沒有辦法可以建造一個陳列室。民國四十五年(一九五六)的春天,兩院得到了美國亞洲協會的幫助,撥款新臺幣六十餘萬元,在庫房的左邊空地上,興建一座陳列室,共有房屋四間,面積共六百平方呎,每次可以展出文物二百餘件,地方雖是小一些,但存臺文物,得以輪流展出,公開參觀了。這個陳列室是四十六年(一九五七)三月開幕的。」
卷一頁247,《文集》載:「建有小型展覽室一間」。
昌彼得《故宮六十星霜》載:獲得亞洲基金會同意補助建造所需的經費新臺幣六十八萬八千元,……到(民國45年)12月落成。這座小型陳列室,……佔地約有一百八十餘坪,……分隔為四間展覽室。
三者加以比較,頁247說是「小型展覽室一間」,似不如昌先生所說「小型陳列室,分隔為四間展覽室」,較合乎實情。按筆者手上就有該陳列室的平面圖,由平面圖顯示有第一室、第二室、第三室、第四室。(見圖一)
圖一:臺中北溝文物陳列室及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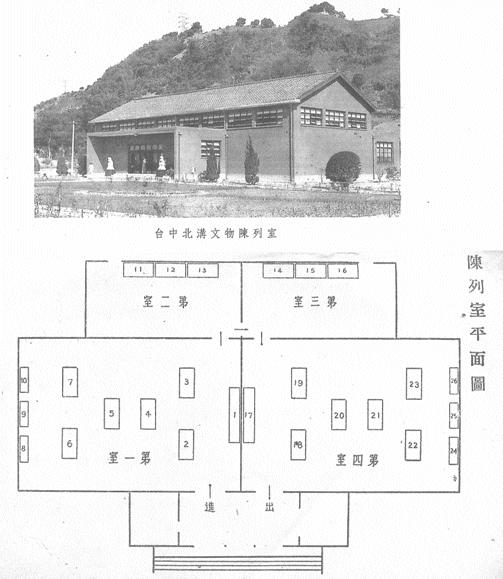
另外,《文集》載建築補助費是六十餘萬元,昌先生說是六十八萬八千元,已接近七十萬元。筆者要補充民國46年3月開幕時,兩院遷臺後第一次文物展覽的內容:分十一類,即銅器、玉器、瓷器、法書、繪畫、圖像、織綉、圖書、文獻、剔紅、雕刻及雜項。共展出304件,編有「展覽目錄」54頁。(附「展覽目錄」封面書影,見圖二)第一期展覽時間始自46年3月24日至4月21日止。昌先生書上說第一個月參觀人數即多達二萬餘人。昌先生的書未寫第一期展出的內容和編有展覽目錄。
圖二:「展覽目錄」封面書影

〔卷二:圖書與圖書館〕補正
卷二頁31,《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2卷4期,係民國16年發行,《文集》誤為15年。
卷二頁156-159,篇名〈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的藏書〉乙文,主旨應以談藏書內容為特色為重點,可惜全文分七段,約1,700字,一至五段涉及藏書的文字只有100字左右,如:「……藏書最多,尤多古書,其價值除國立中央與北平兩圖書館外,幾無與倫比。藏書共有二十餘萬冊之多。」又說:「(八千卷樓藏書)……丁氏經商失敗,亦欲將書出售,日人又想買去,故由兩江總督託繆荃孫向丁氏以十萬銀元購回,此書後即交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故該館所藏古書最為完備。」最後第六段約160字,重複說藏書二十餘萬冊,再說:「抗戰時有書數萬冊送存江蘇興化縣佛寺,全部損失。」最後說留在南京的宋版書並未短少,僅元、明版書及普通書籍稍有遺失等。
總共談藏書文字,約260字,佔全文的百分之十五而已,雖然重點是提到了,但是比例偏低。筆者擬分為三點加以補充。
第一點,《文集》提及購八千卷樓是以十萬銀元成交。筆者查民國17年該館編印《國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小史》(筆者持有者為影印本,乃林清華先生多年前所贈)則說是七萬上千元,相差約三萬元。紀維周〈卓越的圖書館學家柳詒徵〉乙文,說是七萬三千餘元(《劬堂學記》頁290)。吳景文〈中國近代四大藏書家之盛衰〉乙文,說是「以七萬五千銀元之低價,將全部藏書八萬卷,悉售江南圖書館。」(《藏書家》第七輯頁87)許廷長〈柳詒徵振興國學圖書館〉乙文則說:「端方奏請清政府,籌款七千三百餘兩,……購八千卷樓藏書六十萬卷。」四種說法,來不及考證何者為是。《文集》未對這批藏書的特色加以介紹。《圖書館學百科全書》有「八千卷樓」的辭條,介紹其三點特色,請見該書第6頁。前提吳景文乙文,認為丁氏藏書,有四點獨符之處,詳見《藏書家》第七輯頁86-87,在此均不贅述。
第二點,《文集》載:該館藏書有二十餘萬冊,1936年的《申報年鑑》說有21萬冊,較《文集》具體些,不過都是概數。據前提許廷長乙文則詳細多了,許文說:
| 1. | 1927年有藏書177,234冊(內有善本書50,275冊)。 |
| 2. | 1933年到1936年,據《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加以統計,正編收錄館藏。各類圖書198,923冊,補編收書24,926冊。共計223,849冊。 |
| 3. | 戰後,至1946年10月止,統計收回藏書177,428冊,地圖204幅,圖表照片等491份,碑帖132函,字畫144件。許文又說:抗戰前館藏22萬冊書,經過八年戰亂,能收回18萬冊,確實來之不易。特別是八千卷樓珍本的失而復得,更是幸事。事實上,戰後柳詒徵為收回這些圖書,歷盡艱辛,經過數次與蔣復璁先生(任教育部京滬區特派員,兼教育部滬區教育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接收京滬地區敵偽高等教育文化機關學校)力爭,為了爭回館舍而中風。詳見《劬堂學記》乙書相關各文。今謹舉名思想家蔡尚思一段話為例:「後來聽說柳先生復員回南京,以七十老翁奔走收書,甚至為此跪在某掌權者的前面,苦苦哀求才得收回藏書櫃架,復館得原藏書十九萬冊,損失的只十分之一。」 |
第三點,《文集》載:「抗戰時有書數萬冊送存江蘇興化縣佛寺,全部損失」。適才蔡尚思文說損失十分之一,即22,000冊。《文集》又載是數萬冊,中間是有落差的。據林芷茵〈愛書如命的柳詒徵〉乙文所說藏在興化的寺廟和民宅的書(地方志及一些叢書)共約3萬冊(《劬堂學記》頁265)。前提許廷長文講得更詳細,運到興化的地方志及叢書前後裝成107箱,分別藏在觀音閣、羅漢寺、乾明寺。1941年日軍侵入興化,只有將觀音閣所藏部分6,808冊方志及叢書全部焚毀,羅漢寺和乾明寺所藏,於1943年4月被汪偽某副師長搶去,部分散失,1946年初陸續追回一部分。可見並非《文集》所說「全部損失」。
《文集》最後提到戰後國學圖書館元版尚存百分之九十三,明版尚存百分之九十二,則是筆者尚未見過的數字。
卷二頁160,篇名〈運歸國立北平圖書館存美善本概述〉。《文集》載:「這批善本一共有二千八百多種,約二萬一千冊。」張秀民〈袁同禮先生與國立北平圖書館〉乙文說有2,720種,約3萬冊。(文載《北京圖書館館刊》1997年第3期)《文集》同一頁又說,全部攝成影片,共計1,070捲,每捲長達100英尺。同前揭張秀民文則說:「攝製完成膠卷1070卷,長11920英尺」。長度有兩種說法,差異太大,相差九萬五千多英尺。《文集》同一頁又說,去年(民國54年)夏天本館因呈文教育部,建議將該批寄存書運回國,獲得批准。按,並非夏天,而是北平圖書館館長在美逝世(民國54年2月6日)後第四天(即2月10日,公文從承辦、判行、交繕、用印、封發五個步驟一天完成)(見圖三),中央圖書館即密呈教育部轉函駐美大使館交涉運回這批善本書,該公文已刊登民國72年的《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卷1期。
圖三:函教育部洽將國立北平圖書館寄存美國善本運回公文影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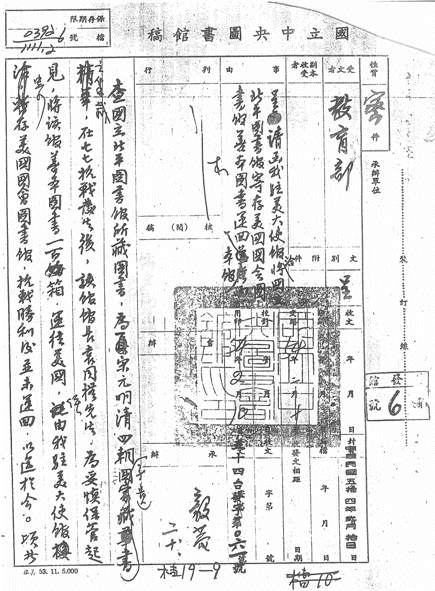
卷二頁161,《文集》載上述這些善本書在美國的照料,攝製微捲的提取工作,均由北平圖書館所派駐的館員王君為之。頁162,又提「王君」一次。按「王君」係指王重民,王重民夫婦(妻子即劉修業女士)於民國36年2月由美返回北京,曾任北京圖書館代理館長,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主任,文化大革命後期,被逼懸樑自盡。同前揭張秀民文說:「攝製工作除美國技師外,館方由當時在美國會圖書館工作的王重民先生負責,每一書皆由他從原裝書箱內取出,加以著錄,並撰寫提要,然後由他交縮微部。縮影完畢後,再由他歸還原箱。」事過境遷,筆者認為還是寫清楚是王重民較好。
卷二頁160-161,《文集》提到運歸北平圖書館存美善本的經過,參與者包括個人五人(美方三人,臺灣一人,中國一人)和三個單位。其中出力較多的駐美文化參事處,只提單位,不提個人。從文化參事張乃維先生給蔣先生的書函(載《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卷1期)中,可看出駐美文化參事處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又以鮑幼玉先生最為辛勞。可是《文集》隻字未提。筆者找到張乃維先生給蔣先生書函原稿,原來是出自鮑幼玉先生的手跡。(附影印本,見圖四)那娟秀的字跡是筆者所熟悉和難忘的(請讀者核對《佛教圖書館館刊》44期,頁123的便函,有鮑幼玉的手跡,請仔細看「席」字的寫法,是否與前揭書函「席」字相似)。三年後,鮑先生返臺任中央圖書館編纂,在館長室上班,偶而下班前會到隔壁期刊股催促鄭恆雄先生和筆者下班,有一次要我們去外頭補習英文,發票交給他去報帳。事隔四十多年,鮑先生早已從臺北藝術大學校長退休,且已辭世多年,但是逝去的往事和娟秀的字跡,令人無限懷念!
圖四:張乃維先生給蔣先生書函原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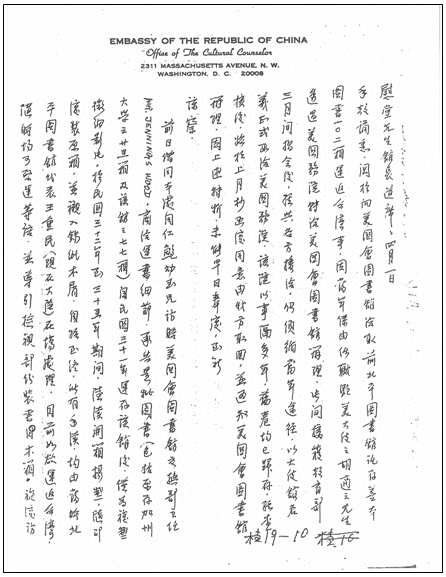
卷二頁163,《文集》的校對頗為粗心,如頁163,誤「蝴蝶原裝」為「胡蝶原裝」,其他頁164,「二百零一部」,印成「二百○一部」;頁165,「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印成「一萬一千○九十五冊」,均欠妥。
卷二頁484,《文集》說民國4年10月教育部公布「通俗圖書館規程」,同年11月公布「圖書館規程」,筆者查過《教育部公報》,兩者都是10月公布的,並令各省11月施行。丁致聘編《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也是說兩者同時公布,同時公布的還有其他社會教育法規,不過丁書載公布日期是18日,筆者查到的資料是23日。
卷二頁485,《文集》載民國15年成立北海圖書館,按係北京圖書館,誤為北海圖書館,民國17年10月才改北京圖書館為北平北海圖書館。從館刊刊名亦可看出端倪。民國17年5月《北京圖書館月刊》創刊,自5期至2卷6期改為《北京北海圖書館月刊》,3卷1期至6期改名《北平圖書館月刊》,自4卷1期起改為《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事實上,《文集》頁621,即載有民國15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在北平北海成立北京圖書館。
卷二頁576,《文集》載蔣先生自1923年在北平參加松坡圖書館工作,擔任北平圖書館協會書記,1926年起參加北平圖書館工作。又誤把北京圖書館為北平圖書館,擔任北平圖書館協會書記應該是1924年的事,因為「協會」1924年才成立。同時協會名稱似是「北京圖書館協會」才對。當作一個地名,《文集》對「北京」和「北平」分不清楚的例子,不勝枚舉。看到先生自題輓聯中有「勞勞不息」、「嘗盡甜酸苦辣」,筆者內心只有崇敬,豈敢苛責這些芝麻小事。
卷二頁602,《文集》列舉多所圖書館出版的目錄、索引和期刊,大部分的書名都不完整,如載「中央圖書館出版過重慶各圖書館所藏西南有關圖書聯合目錄」,正確書名為《重慶各圖書館所藏西南問題聯合書目》;又載:「印行抗戰期間國民必讀書目六輯」,此書名疑為《戰時國民知識書目》;又載「印行英文書林季刊」既然是英文期刊,宜加注英文刊名,該刊英文刊名為:Philobiblon ; A Quarterly Review of Chinese Publications(按《國立中央圖書館六十年大事記(初稿)》Chinese誤刊為Chiness),其實,正確的著錄方法是先著錄英文刊名,再加注中文刊名。
卷二頁621,此頁疏誤較多。《文集》載「後來中華圖書館協會,於十四年(1925)四月在北平開成立大會,梁任公先生被舉為董事長,袁守和先生任執行部長,我任執行部幹事」。錯誤之一:4月25日中華圖書館協會成立於上海,6月在北京舉行成立儀式。《文集》6月誤為4月。錯誤之二:梁啟超被舉為董事部部長,非董事長,時間是5月27日。錯誤之三:袁同禮非執行部部長,部長是戴志鶱,因戴氏要出國,11月才返國,這段期間由袁同禮代理部長之職。又,執行部幹事有三十三人,蔣先生是其中之一人。另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均誤為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兩次)。頁621有九次提到「北平」,宜改為「北京」,奇怪的是蔣先生編〈先叔百里公年表〉(收在《蔣百里先生全集》乙書內),均稱「北京」,《文集》卻大部分稱「北平」。
卷二頁622,《文集》載蔣先生編〈四書集目〉及〈孟子集目〉兩種,漏最早編的〈論語集目〉,這3種「集目」都收在《文集》卷二頁1-31,原刊載《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文集》刊名誤稱《中華圖書協會報》,漏「館」、「會」二字。這一頁還是有些錯誤和疏失,如:梁啟超起草的是「中國圖書大辭典計畫」,非「圖書大辭典計畫」,《文集》又載:「我將我的主張在北京圖書館月刊第二期發表了」,蔣先生漏寫題名:關於中文編目之通訊,亦非在第二期發表,是在第三期發表。又說在中華圖書館協會第一次年會發表論文的題目是「中文圖書分類之商榷」,題名錯一字,漏二字,正確的題名是「中國圖書分類問題之商榷」,又誤寫中國目錄學史作者姚名達為姚明達。
卷二頁623,民國22年1月,蔣先生接到教育部的派令,任國立圖書館籌備委員,非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委員。公文無「中央」二字。改籌備處主任時,才有「中央」二字。
卷二頁626,《文集》載:「從民國三十年至三十二年止,在上海收購了大批圖書,最著名的藏家是適園張氏、嘉業堂劉氏、江寧鄧氏、番禺沈氏等家。」購書始於民國29年初,止於30年底。30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開始進佔上海租界,宣告上海「孤島」最後淪陷,大學紛紛關閉。購書都是靠鄭振鐸(筆名西諦、鄭西諦)為主,鄭先生開始疏散自己的藏書,並改名,拿假身分證,已離家避難。民國31年1月,日本當局宣布接管上海租界七大公用事業,市面開始缺糧;2月,日人開始調查戶口;3月,鄭先生友人陸續被日軍逮捕;8月,上海實施燈火管制。民國32年,鄭先生只能個人零星購書、讀書、著述和編書。自民國30年底起已不再替中央圖書館購書了。
筆者認為蔣先生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沒有把抗戰陷區搜購珍本的來龍去脈講清楚。購書檔案已被利用,發表在期刊,成為專書的一部分,或寫成學位論文了。中央圖書館五十周年館慶出版的《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卷1期都公布了蔣先生給教育部的購書簽呈(民國29年2月27日),也公布了教育部給蔣先生的機密公文,還刊登自民國29年至30年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的第一號至第九號的工作報告。圖書館出版的大事記都已刊載蔣先生是民國29年1月1日啟程飛香港的,14日已和張元濟、張壽鏞、何炳松見面商討購書事宜了。最重要的是,鄭振鐸的〈求書日錄〉都已出版了,還有什麼可隱瞞呢?
同一頁及頁627,兩次提到陳群的澤存文庫,是澤存書庫才對。又載接收日本同文書院的圖書,同文書院前宜加「東亞」二字。
卷二頁627,提到幾個國立圖書館的成立是蔣先生「戰後主張設立的」,這又與事實不符,國立蘭州圖書館的前身是國立西北圖書館,該館抗戰期間就成立了。又說擔任教育部京滬特派員時,對圖書查明來源後,統統發還了。就國學圖書館來說,圖書是歸還了,但是其過程並不順利,與蔣先生的說法是有出入的,《劬堂學記》乙書中有多篇文章支持筆者的看法。
卷二頁628,在臺中成立「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文集》在「館」之前漏「院」字。《文集》又載蔣先生於40年5月返臺,返臺應改為來臺。《文集》卷二頁723,第二行即寫「來臺之後」。
卷二頁629,蔣先生把能做點事的原因,歸納成兩點:第一,依賴天主賞賜的恩寵;第二,仰賴長官、前輩同仁、朋友的幫助。第一點只能在教堂說說,第二點要靠運氣,是可遇不可求的。筆者也試提三點淺見:第一,要仰仗基層同仁旺盛高昂的士氣和激發全體同仁的潛力;第二,不要任用只會迎合和做表面功夫的單位主管;第三,有使命感的館長,有發展的總目標。
卷二頁701,〈中國圖書館員的教育問題〉乙文說:「民國十年Mary E. Wood女士在武昌大學設立圖書館科,……民國十六年文華大學的後身──華中大學停辦此科,圖書館專科單獨成立學校,她招收各大學轉學的三年生,肄業兩年,名為專科,等於大學。」按,蔣先生在《文集》卷二頁488,另有說法:「民國八年美國人韋棣華女士(Miss Elizabeth Wood)創辦的武昌文華大學圖書館學專修科,即是現在的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
這兩段文字,加以對照,有所不同:
| 1. | 時間不同,一說民國10年,一說民國8年。 |
| 2. | 校名、科別不同,一說武昌大學圖書館科,一說武昌文華大學圖書館學專修科。 |
| 3. | 同一位外國人,有的無中文譯名,有的加中文譯名。 |
筆者在《中國近六十年來圖書館事業大事記》乙書中,認為是民國9年3月文華大學圖書科成立,依據的資料是武昌該校的《文華圖書科季刊》1卷1期,頁107-109。民國14年文華大學改組為華中大學,16年該大學停辦此科,圖書科單獨成立學校。最後改名為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那是民國18年8月的事。
至於《文集》對Miss Elizabeth Wood,出現三種譯名,有譯為韋棣華者(卷二頁565),有譯為伍德小姐(Miss Wood)者(卷二頁722),有譯為華德Miss Wood者(卷二頁883),《文集》書後如果編有索引,可避免這些困擾。
卷二頁702,篇名同頁701,該文說:「北京大學最先在三十七年辦了圖書館科,凡各院系學生願習圖書館學的,可在該科加修七十學分,考試及格,即可加得圖書館科畢業文憑。」
筆者根據《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1114)的說法是:1947年秋,國立北京大學奉准創辦圖書館專修科,附設文學院內。科主任為王重民。他院學生選修課程滿72分,成績總平均70分以上者,給予畢業證書。
另一種說法是2003年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系編《王重民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乙書內四名學者大同小異的看法:
| 1. | 周文駿:1947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籌建圖書館學專修科。 |
| 2. | 來新夏:1947年在北大創建圖書館學專修科。 |
| 3. | 朱天俊:(1947年)在中文系附設了圖書館科,招收中文、歷史、哲學、教育等系畢業或肄業學生學習兩年,辦了兩屆。 |
| 4. | 李世娟:1947年2月,王重民先生從美國華盛頓取道上海,旋即北上到北平,向胡適先生提出辦圖書館學專業的建議,被採納。起初由於經費等方面的限制,附屬於中文系,招收對象是中文、歷史專業的畢業生,成績在75分以上即可直接進入圖書館學專修科學習,學生學習圖書館學、目錄學基本課程,修滿32個學分即可授予圖書館學專科的學士學位。 |
東海大學圖書館編印的《圖書館學報》11期(頁1)稱國立北京大學辦圖書館科在民國37年,與蔣先生的看法是相同的。
以上諸說並陳,有待進一步去探討。
卷二頁722,《文集》載:政府利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興辦了清華學校,還在「民國十三年花一百萬元建造了國立北平圖書館」。短短一行,不過20字,卻有多處疏誤:
| 1. | 民國13年只有京師圖書館,17年才有國立北平圖書館這個館名。 |
| 2. | 未講明給錢的機構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該董事會民國13年9月才成立。 |
| 3. | 給錢的時間是民國15年,該年1月26日董事會舉行第一次年會決議的。 |
| 4. | 受補助的單位是民國15年成立的北京圖書館。《文集》只有一個地方講對,即一百萬元,惟仍可找出小毛病,《文集》未具體講清楚是「建築設備費」。事實上,民國16年9月該董事會又通過增加北京圖書館建築費二十五萬元,購書費三十萬元。 |
該董事會也有補助國立北平圖書館七十萬元,「建築一中西合璧,美奐美侖的中國最大的圖書館;又撥款購置中西文普通圖書及經常費用」。(見卷二頁569,不過這一頁說「這個京師圖書館即於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與中華文化基金董事會訂約,……」又兩處疏誤,民國18年已無京師圖書館,董事會的全名也講錯了)
卷二頁723,講臺灣的圖書館教育,《文集》載:「至教育部申請在師大中文研究所設圖書館主修科,有六人畢業」。此行文字,講錯研究所名稱,文字又語焉不詳。今摘錄六人畢業生之一的喬衍琯教授的一段回憶錄,加以補充:「臺灣師範大學在四十五年秋創設國文研究所,次年春招收第二期研究生,分為三組,其中一組是目錄學組,與中央圖書館合作。……三月開學,上午在所受業,課程比一般研究生要多,共修十二門課,四十八學分,一半是圖書館方面的。……下午在圖書館實習,不但訓練出工作能力,也培養出對圖書館的興趣。師大國文所的這一期目錄學組,可說是我國第一所關於圖書館學的研究所,……」(原載《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23卷2期,篇名〈追憶蔣慰堂老師〉)。
卷二頁728-729,《文集》載:「當我學校畢業,應清華大學之聘前往執教,仍然在原處工作。及至北平圖書館創辦成立,復在北平圖書館工作十年。後赴德國求學,一面讀書,一面在圖書館工作。回國後於民國二十一年,奉教育部之派,承乏籌辦國立中央圖書館。」按,蔣先生民國1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民國13年至清華學校任教,非清華大學,民國17年8月17日清華學校才改為國立清華大學,首任校長為羅家倫。《蔣復璁口述回憶錄》(頁35)也說至清華大學任教,都是欠妥的。《文集》說仍在原處工作,指松坡圖書館。《文集》又載:「及至北平圖書館創辦成立,復在北平圖書館工作十年」,按,前面所稱北平圖書館,是指北京圖書館,民國15年才成立。昌彼得〈蔣慰堂先生年表〉載:「(民國十五年)是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建立北京圖書館完成,聘梁啟超先生為館長,袁同禮先生為圖書部主任,先生亦轉任職該館。」民國18年6月該館與國立北平圖書館合併,蔣先生繼續留下來工作,一直到19年7月赴德留學,在北京圖書館、國立北平圖書館兩館工作不到四年,《文集》說是十年,如果是從民國9年冬參與蔣百里興辦的讀書俱樂部起算,(昌彼得〈蔣慰堂先生年表〉認為這是「先生與圖書館發生淵源之始」)到民國19年,前後有十一年,扣除在北大讀書期間,休學一年,則有十年。
《文集》又載:「回國後於民國二十一年,奉教育部之派,承乏籌辦國立中央圖書館」,22年誤為21年,是明顯的失誤。
卷二頁862,《文集》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是民國十六年由傅斯年先生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兼國文、歷史兩學系主任,並文學院院長時創設的,稱為語言歷史研究所」。頁863又載:「十六年春傅(斯年)先生到校,秋天就開始設立語言歷史研究所」。這兩段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史實,不過,寫法仍有小缺失。第一段要加中研院史語所的「前身」是中山大學的語言歷史研究所。一定要加「前身」二字。第二段載「秋天開始設立」,這種寫法並不多見。一般都寫什麼時間成立、創辦、建立,或成立、創辦、創始於什麼時間。如果要寫開始成立、開始籌畫,相對地就要寫什麼時間正式成立。未見過只有寫「開始成立」、「開始設立」的。查寫這一段史實的著作,都寫民國16年秋「創辦」(如李泉《傅斯年學術思想評傳》)、「創立」(如《民國百人傳》、焦潤明《傅斯年傳》、《傅斯年董作賓先生百歲紀念專刊》)。筆者認為上述兩段文字可以合起來寫,寫法可參考《中央研究院史初稿》(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秘書組編印,1988年)乙書的寫法:「該所(歷史語言研究所)前身為民國十六年夏間大學院設於廣州中山大學之語言歷史研究所,本院成為獨立機構後,改名歷史語言研究所。」這裡寫「十六年夏間」,《民國人物小傳》(傳記文學出版社)第一冊,也有相同的寫法,即:「其年(十六年)夏,在該校(中山大學)創立語言歷史研究所」。《傅斯年學術思想評傳》載1927年8月創辦了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如果是8月初,屬立秋前,也算是夏天。
以上所提只是為了「前身」、「開始」四字的增刪的芝麻小事而已,因為筆者偏愛大事記類的工具書,才有此看法,如有浪費讀者寶貴的時間,懇請見諒。
卷二頁873,《文集》載:「民國二十二年一月間……,教育部預備成立中央圖書館,派我擔任籌備委員會委員」,按,派令是寫「國立圖書館籌備委員」,無「委員會」三個字。昌彼得〈蔣慰堂先生七十年表〉、〈蔣慰堂先生年表〉二文,均寫成「教育部派先生為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五字為贅字,宜刪。
卷二頁885,《文集》載:「回到南京後,……此時中央圖書館所庫藏的中西文書籍已達一百萬冊。」筆者據〈國立中央圖書館復員以來工作述要(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已完成登錄的圖書加以統計,包括:中日文圖書、西文圖書、中文期刊、西文期刊、報紙五部分,共有945,750冊,尚有部分未整理和待登錄,其中陳群的澤存書庫有中日文圖書三十七萬一千餘冊,尚有部分中日文圖書和西文圖書待登錄。頁885又載:「民國三十四年九月我回京後,立刻又到上海去察看在戰時所收購的珍本圖書。」據鄭振鐸的日記,蔣先生是9月10日抵達上海,當天即與鄭振鐸、徐森玉見面,11、12、13日又連續三天與鄭振鐸見面,20日又見面一次。9月23日赴南京。這幾天蔣先生應看過珍本圖書的存放地點,應約略知道還有多少箱未整理,預估何時可全部運到南京。這一部分,《文集》均未見說明與交待。
《文集》頁885和頁891,稱陳群的藏書處為澤存書庫,是對的;《文集》頁572和頁626,以及《蔣復璁口述回憶錄》頁60,均稱為澤存文庫,是錯的。
卷二頁926,《文集》載:
民國二十九年,抗戰正酣之際,淪陷區之文獻故家,以生活日漸艱困,所藏珍本古籍,無力世守,紛紛出售,流入市肆。滬上有識之士,聞悉美日等國大學圖謀籌款收購,懍於清季歸安陸氏皕宋樓之珍藏售歸日本岩崎氏之殷鑑,深虞國家文化資產流散域外,乃聯名函電陪都教育部及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請迅予設法搶購。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長朱家驊先生以機不可失,力主收購,並主張動用該會補助國立中央圖書館南京建館經費而尚留存之法幣壹百數十萬元,以充購書經費。教部代理部務之顧毓琇次長亦極贊成,未幾出巡返部之陳立夫部長欣然同意,且表示在經費方面,願全力支持。余因啣命由渝飛港,首訪晤中英庚款會葉譽虎董事,請其在港設立機構,收購南方散出之珍籍與主持轉運事宜。然後易換名姓,潛往上海。與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兩先生密議,委託主持江南地區圖書收購事宜。獲滬上教育學術界之鼎力支助,搜購之事甚為順利,短期之內購獲之舊籍不下十餘萬冊,半屬善本。
按《文集》中類似上述引文講抗戰陷區購書的文章,至少有十四篇以上,其中有兩篇專文,有十二處是像頁926一樣,是屬於一篇文章中的一部分或一段。筆者特地把這些文章全部複印,集中閱讀,再詳加比較,得出的結論,令人感到意外。至少有三點疑惑:
第一點,沒有一篇或一段較長的文字把整件購書過程或來龍去脈,交待得一清二楚,反而說法不一,且出入很大。如:領銜提議和連署的人是誰,有多少人,什麼時間發電報或寫信,共有幾次,接收的人是朱家驊或陳立夫,蔣先生從重慶出發和回來的時間,到香港和上海的時間,離開上海的時間,在上海停留幾天,在上海與什麼人接觸,除給教育部的公文外,為什麼不提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那九次工作報告的內容,實際參與者共幾人,他們如何分工,哪幾位始終參與其事,何時開始搜購,何時結束,搜購的善本佳籍數量多少,搜購哪些大藏書家的收藏,搜購的珍本佳籍存放何處,如何整理和寄送重慶,抗戰結束後寄放香港和上海的珍本圖書有全部運回南京否,如有未運回南京,這批書的下落如何,購書費用有多少,款項如何交給上海的工作人員。其中最令人疑惑不解的是整個始末,鄭振鐸參與最多,是最重要的主角,為何至少有十四篇文章似有意避談鄭振鐸,鄭振鐸的日記多次提到蔣先生,給蔣先生很多信都提到購書乙事,說明他們關係密切,但在《文集》中只出現過兩次,一次稱「鄭西諦」,一次稱「鄭先生」,只有《蔣復璁口述回憶錄》乙書中,唯一出現過「鄭振鐸」三個字,連與蔣先生情同父子的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和曾任中央圖書館特藏組主任的昌彼得先生,在〈蔣慰堂先生七十年表〉、〈蔣慰堂先生年表〉、〈蔣慰堂先生與國立中央圖書館〉諸文章中,也避談提「鄭振鐸」這位陷區購書貢獻最大的學者,是有什麼祕密嗎?不然怎麼張壽鏞和何炳松也都參與購書乙事,為什麼提到名字都超過十六次以上,落差未免太大。
第二點,蔣先生寫這些文章時為什麼未見引用從南京帶來的檔案,這些檔案約四十年前筆者在圖書館因無事可做(與當時的館長鬧翻),就每天從編目組走到特藏組,去看那從未打開過的19箱檔案,順便把圖書部分,取出放到書架上,最後剩下13箱。這些檔案讓筆者大開眼界,看到筆者最崇拜的《圖書學館要旨》的作者劉國鈞先生的書信和未刊稿(影印一份,見圖五),看到筆者在師大的老師王省吾和藍乾章貼在履歷卡上的照片,還有當時筆者的頂頭上司編目組主任林愛芳女士貼在履歷卡上的大學畢業半身照片,長得漂亮又甜美,此照片並未帶來臺灣,她真是喜出望外。筆者再回頭說,這些重要檔案有很多與陷區購書有關,像包括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的第一號至第九號工作報告已刊載《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五十周年館慶特刊,劉顯叔先生主編)新16卷1期,還有蔣先生民國29年2月27日給教育部(或中英庚款董事會)的機密簽呈,也刊登在同一期的館刊上。不知蔣先生為何不加以利用或引用。這十四處談陷區購書的大事,令人感覺是憑記憶寫的。靠記憶寫文章,是不可靠的。
圖五:劉國鈞先生未刊稿影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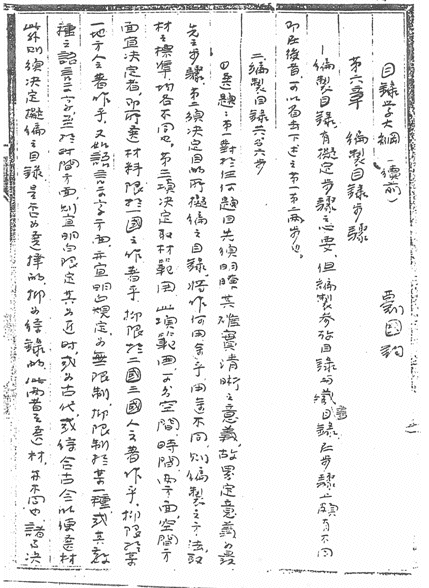
話再說回來,老同仁應知蔣先生寫陷區購書的事,也會看過這些文章,為什麼不主動提醒要參考這些檔案,要看看鄭振鐸寫的那麼多書信和工作報告,如果當初蔣先生有先看這些檔案,應可避免很多錯誤。圖書館員要服務讀者,應包括首任館長在內。記得筆者當時發現檔案中有蔣先生兩篇未刊稿,立刻複印後送到故宮博物院,不久就同時刊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7卷2期,文章開頭還特地寫一段話:此二文皆由舊檔內覓得,雖皆為抗戰期間所作,明日黃花本無再發表之必要,但由此二文可見抗戰期間中國圖書館書業之狀況而過去許多事實均可藉以明瞭,則不無有參考之價值也。(附兩篇原稿首頁影印本,見圖六、圖七)
第三點,蔣先生似無個人日記,服公職時,服務單位應有工作日誌,辦公廳一定有週曆本,記載每天行程和會議,蔣先生離職或退休時秘書單位應把週記本的影印本和加洗的有關照片送給蔣先生,以備日後寫回憶錄或接受訪問的參考。中央圖書館第三任館長包遵彭辭世後,包夫人把包館長生前放在辦公桌上的週曆送給筆者,上面記載開會、宴會、會客、上課、演講的時間、地點、人物等。有這些材料做基礎,將來寫回憶錄或口述歷史時,對關鍵的問題,較不易弄錯。
圖六:〈抗戰四年來之圖書館事業〉稿本影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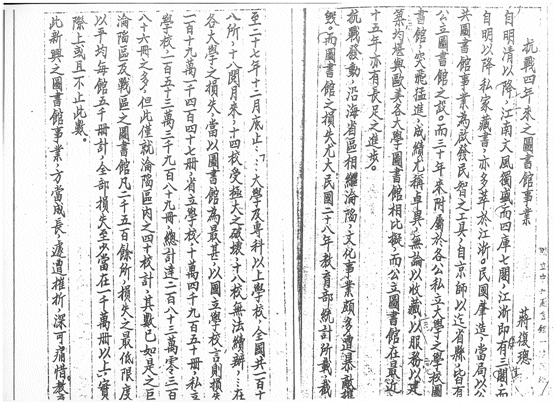
圖七:〈中國圖書館事業的回顧與展望〉稿本影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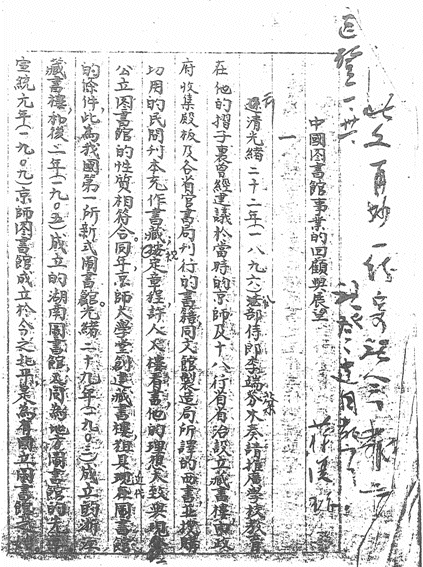
既然上述諸問題,均未妥善處理,《文集》載有關陷區購書的十四篇文章會發生許多說不清楚、講不明白,就不會令人感到意外了。事情總要弄清楚,問題總要解決,筆者先從十四篇文章中歸納出九個問題,每個問題都把不相同(少數相同)的看法並列,至於是非對錯,留待以後討論。行文時只有引用較重要的文字時,才注明頁碼。另有下列兩篇蔣先生的文章未及參閱,似會談到陷區購書之事:1. 〈六十年的圖書館員生活〉,載《傳記文學》47卷5期,以及《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37期;2. 〈蔣復璁與圖書館事業〉,載《東方雜誌》21卷8期至22卷8期(中間有中斷)。
1. 搜購圖書的倡議者
發起搶購的人士,張壽鏞、何炳松各提兩次,鄭振鐸一次,其餘均稱「上海學人」、「有心人士」、「有識之士」、「文教界人士」、「教育學術界許多先生」。這一部分,有的講太少,有的講得過於籠統。實際上,倡議者至少有五人可列出姓名,鄭振鐸〈求書日錄〉說:「我和當時留滬的關心文獻的人士,像張菊生、張詠霓、何柏丞、張鳳舉諸先生,商談了好幾次,我們對於這個『搶救』的工作,都覺得必須立刻要做!我們乾脆地不忍見古籍為敵偽所得,或大量的『出口』;我們聯名打了幾個電報到重慶。我們要以政府的力量來阻止這個趨勢,要以國家的力量來『搶救』民族的文獻。」由此看來,答案是由鄭振鐸領銜發起的。倡議的方式,有「函電」、「致電」、「函」、「寫來的信」四種說法。
2. 贊同購書的中央要員
大部分提朱家驊(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長)和陳立夫(教育部長),有時也提到教育部次長顧毓琇(一樵)。
3. 搜購單位
政府交由中央圖書館辦理搜購,因為中央圖書館有一筆建築經費留在中英庚款董事會,此時已開始通貨膨脹,不用的話,即貶值。
第二、三個問題,《文集》的說法是一致的。
4. 時間問題
| (1) | 蔣復璁出發的時間:民國29年冬提了三次,29年底一次,29年冬間一次,29年一次,大部分只提「抗戰時期」。較詳細的是卷二頁875:「二十九年底,由重慶飛往香港,……三十年一月十日抵上海,……二十日離開上海」。以上都是錯的。較正確的說法是蔣先生給教育部的簽呈,日期是民國29年2月27日,簽呈上說「(二十九年)一月一日職由渝赴港,……十四日到滬,……職因於本月(二月)一日回渝。」 |
| (2) | 蔣先生在上海停留時間:停留九日(卷二頁625、頁951),住了十天(卷二頁875)。 |
| (3) | 蔣先生離滬時間:有四種說法。 |
| A. | 卷二頁875,說是30年1月20日,此與蔣先生給教育部的簽呈說是民國29年2月1日回渝不符。 |
| B. | 兩次(〈一剎那中的決定〉、〈國立中央圖書館創辦的經過與未來的展望〉二文)提到民國29年農曆12月23日離滬,換算陽曆為30年,亦與給教育部簽呈的日期不符。 |
| C. | 一次提到夏曆12月下旬(〈涉險陷區訪「書」記〉,《中央月刊》2卷9期),換算陽曆也是民國30年,錯誤同前。 |
一次(〈我與中國的圖書館事業〉乙文)只提夏曆12月23日,未提哪一年。換算陽曆是29年1月31日和30年1月20日。前者算是第四種說法。年、月是沒有問題的,31日是不可能的,給教育部的簽呈是說2月1日返渝。從上海乘船到香港,在香港與蔡元培見面,再飛回重慶,短短一兩天是辦不到的。這樣算的話,等於在上海停留十六天,與《文集》所說在上海停留十天、九天,也不符。後者的時間同第一種說法,昌彼得亦支持這種說法。這一種說法,很顯然民國30年是錯的,1月20日是很有可能的。據鄭振鐸〈求書日錄〉乙文和陳福康《鄭振鐸年譜》乙書,蔣先生是在20日、21日、22日三天中的某一天離開上海的。蘇精〈抗戰時期秘密搜購淪陷區古籍始末〉(《近代藏書三十家(增訂本)》,中華書局,2009年4月)乙文,說是1月23日離滬,未知其資料出處為何,是否據蔣先生所說1月14日抵滬,待了九天,所以說是23日離開。筆者認為多多核對原始史料(如日記、檔案),離滬日期的確切時間,應不難查出。
| (4) | 會見蔡元培的時間有兩種說法,一是卷二頁951,說民國29年1月31日,離滬到港,見到了「蔡孑民老師(時任中央研究院長,在香港養病),我報告了採購陷區流出善本圖書事,他也很贊成,不意我離開香港兩星期,蔡師就因病逝世。」蔡院長是3月5日逝世,與蔣先生所說中間相差一個月,蔣先生不可能在香港待一個月。一是卷五頁5,說民國30年1月20日(假設是29年1月20日亦可)「我在香港,與陳仲瑜兄同去看了蔡孑民先生,……那知我回到重慶一星期,他就病故了,……後來我特別寫了一篇追悼文字,載在重慶中央日報特刊。」無論如何,1月底距蔡院長辭世,還有一個月又四天,說成「一星期」未免離譜,如果是30年,就更加離譜了,因為蔡院長在民國29年就逝世了。不過蔣先生說在《中央日報》特刊寫追悼文章乙事是事實,這篇文章刊載重慶《中央日報》29年3月24日出版的「蔡元培先生追悼紀念特刊」上,蔣先生撰寫的篇名是〈追念蔡先生〉(按〈蔣復璁先生著述年表〉和《國立中央圖書館同人著作目錄》蔣復璁部分均漏收此文)。撰文者還有吳敬恆、王世杰等,又重刊蔡院長〈我在教育界的經驗〉乙文。 |
5. 接洽及承辦者
民國29年1月,蔣先生到港滬找哪些人士洽商搜購珍本圖書,並進一步如何執行,如何任務分工等,據《文集》所載,除香港方面都說是由葉恭綽(中英庚款會董事)負責蒐集流入香港的珍籍,兼主持上海購書轉運重慶的事宜。有一次提到由簡又文負責經營;上海方面,與誰接洽、由誰承辦、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扮演的角色等,《文集》的記載,說法出入較大。筆者粗略統計人名出現的次數,計張壽鏞(詠霓)十七次,何炳松(柏丞)十六次,張元濟四次,鄭振鐸兩次(鄭西諦、鄭先生各一次),徐鴻寶(森玉)兩次(一次說善本由其鑑定,一次說帶錢去上海),李拔可一次。有些文章,人名後加「等」字,就無法統計,有些未提人名,也無法統計。至於商討的對象與工作性質,用詞均欠一致,舉例如下:
| (1) | 與張壽鏞、何炳松等洽妥……。 |
| (2) | 與張壽鏞、何炳松等密商負責京滬平津一帶……。 |
| (3) | 並得張詠霓、何柏丞兩先生之贊助。 |
| (4) | 與張壽鏞、何炳松兩先生密議,委託主持江南地區圖書收購事宜。 |
| (5) | 到了上海,見到何炳松與張壽鏞,遵教育部中英庚款董事會共同決定,請張、何二先生主持,……上海方面因為暨南大學遷離上海,因此,何、張委託鄭西諦辦理,後來張逝世,於是全部由鄭先生負責,善本由徐鴻寶鑑定。(見卷二頁951) |
| (6) | 上海何炳松、張壽鏞負責。 |
| (7) | 蔣復璁給教育部簽呈:香港與葉恭綽會商搜購散失舊籍,(29年1月)14日到滬,由商務印書館張元濟、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三人負責主持。 |
| (8) | 〈一剎那中的決定〉(卷五)乙文中,提到接洽與幫忙的人有五位:張元濟、張壽鏞、何炳松、李拔可、何德奎。獨漏訪購珍籍不遺餘力的鄭振鐸,也漏提早期與鄭振鐸一起負責採訪工作的北京大學教授張鳳舉。 |
| (9) | 《蔣復璁口述回憶錄》乙書,只寫與何炳松、張壽鏞密商,主持收購事宜。 |
上列九種說法,用詞不一,有「洽妥」、「密商」、「協助」、「委託主持」、「主持」、「辦理」、「負責」等。到底有多少人參與,有二人、三人、四人、五人、或加「等」字,共五種說法。筆者以為上列諸人士都是精通目錄版本之學,是大學者,是文獻學家,也是藏書家,對江南藏書家和古籍市場的負責人素有來往。同時,在淪陷區工作,除了學識外,還要有膽識。搜購任務異常艱鉅,非一般人所能勝任,其擔任的工作只是「協助」、「辦理」、「委託主持」等一般事務工作的普通用語,是有欠公允的。對出力最多,工作不遺餘力的第一人──鄭振鐸並未特別表揚,令人感到不平。事實上,蔣先生應該引用民國30年1月20日,徐森玉致蔣先生的信,提及鄭振鐸等為搶救文獻「心專志一,手足胼胝,日無暇晷,確為人所不能;且操守堅正,一絲不苟,凡車船及聯絡等費,從未動用公款一錢」。(原信存中央圖書館)陳福康著《一代才華:鄭振鐸傳》乙書中,提到鄭振鐸除了必須到暨南大學上課外,其他時間便幾乎全撲在搶救古書上了。書中也引用鄭振鐸自己寫的兩段話:「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瀾,誠哉其為愚公移山之業也!杞人憂天,精衛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從!」「我要把這保全民族文獻的一部分擔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決不放下。我做了許多別人認為傻的傻事。但我不灰心,不畏難的做著,默默地躲藏的做著。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每天這樣的忙碌著,說句笑話,簡直有點像周公的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有時也覺得倦,覺得勞苦,想要安靜的休息一下,然而一見到書賈們的上門,便又興奮起來,高興起來。」
6. 購書的起訖時間
《文集》所載有:「自三十年起」、「經三年之久」、「三十年至三十二年止」、「自三十年起,至抗戰結束」,共四種說法。實際上,只有民國29年至30年底,兩年而已。
7. 購書費用
來源有兩筆,一是中英庚款董事會撥作中央圖書館的建築費留存的款項,《文集》一說「一百數十萬元」,一說「一百餘萬元」,一說「一百二十萬元」,共有三種說法。建築費全部用罄,教育部的撥款約有二百萬元,說法是一致的。
8. 購書的數量
《文集》所載只有兩筆資料,同時所說的兩組數字相差太大,一說「一共收購了四、五萬冊」,一說「購獲之舊籍不下十餘萬冊,半屬善本」。一件大事,竟然未有一較準確的數字,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筆者合理的懷疑:尚有部分購書未運到南京,所以無法統計。他人撰寫的文章,提及此事,說法也不一致。如蘇精〈抗戰時期秘密搜購淪陷區古籍始末〉乙文說:「單是甲乙兩類的善本古籍就有四千八百六十四部,共是四萬八千多冊,普通本線裝書更多,有一萬一千多部」,這是目前所看到最具體的數字。沈津〈佇中樞以玄覽 頤情志于典墳──談《玄覽堂叢書》〉乙文(收在《書城風弦錄──沈津學術筆記》,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則說:「從1940年至1941年的兩年中,……從私家及舊書店為中央圖書館代購善本約3,800種,這個數字差不多相當於三四十年代北平圖書館數十年之積累。」陳福康《一代才華:鄭振鐸傳》乙書中說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的購書活動進行了年餘,「以不到百萬元之款買下了大量的有用書籍,其中可進入高標準的『善本』之庫的,就已有四千種左右。已經抵得上當時苦心經營了幾十年的北平圖書館的善本庫的總數了」。
9. 購書是否全部運回南京
前文提到整個購書過程,《文集》尚未交待清楚的,其中之一即購書是否全部運回南京的問題,有交待香港購買的書,《文集》卷二頁951:「我(蔣先生)先到香港,遵朱先生命,見到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葉譽虎先生,託他負責收購流入香港的善本圖書,他委託簡又文先生經營,在我離開大陸前,此批書迄未運返南京,大陸淪陷後,不幸也為共匪接收去了。」
至於存放上海部分是否全部運回南京,《文集》無片紙隻字的說明,只說抗戰後曾到上海去看過這些書。國內有幾篇談這一段歷史的文章,均未見明確指出所有存放上海的藏書是否全部運回南京;也未說明,最後一批啟運的時間和種數、冊數。據吳岩在《鄭振鐸紀念集》(上海魯迅紀念館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年)乙書中的幾篇文章,和鄭振鐸的兒子鄭爾康著《石榴又紅了──回憶我的父親鄭振鐸》乙書所寫,均明確指出:保存在覺園法寶館的藏書有一批(一說近百箱)並未運回南京,而屬於「人民政府所有」。這是一件令人震驚的消息。筆者認為蔣先生也一定知道此事,因為「南京的圖書館幾次來電催促」,鄭振鐸先是「故意讓助手們放慢整理的進度」,後來對南京的催促,鄭先生「都淡淡地跟助手說:『不睬它就是了。』後來他們就是整理好了,鄭振鐸也不叫運了」。(見前揭書頁316)筆者初步判斷這是《文集》避談鄭振鐸的真正原因。另外,《文集》在十四篇文章中,除蔣先生給教育部的簽呈中有提到在上海成立「文獻保存同志會」外,似未見提到該會對陷區購書的貢獻,這也是讓人想不透的事。
以上九個問題,大部分均可進一步去深入探討,以期真相能早日水落石出,還給真正有貢獻者一個公道。
卷二頁927,《文集》載:「當善本書收購時,因其中不乏祕笈,尤以明代史料孤本為多,深懼在戰亂中轉運難免遭受不可抗力之損害,遂由徐森玉先生主持,選擇若干孤本,隨時攝成照片,以備陸續影印,而廣其傳。第一批選印三十三種,裝訂成一百二十冊,命名曰『玄覽堂叢書』,凡明刻二十六種、清刻一種、明清舊鈔六種。自文獻言之,除元代一種外,概屬明代史料。初輯出版於民國三十年,首冠玄覽居士序一篇,即係徐森玉先生主筆。序題『庚辰夏』,木記題『庚辰六月印行』。庚辰為民國二十九年,推前一年者,蓋避日方耳目也。」
按,《文集》認為《玄覽堂叢書》是由徐森玉主持編選。撰寫〈玄覽堂叢書提要〉、〈玄覽堂叢書續集提要〉、〈玄覽堂叢書三集提要〉的顧廷龍卻說:「國立中央圖書館遂請鄭振鐸先生在滬蒐採之,並選元明以來著述傳本罕見者,輯為《玄覽堂叢書》,以廣流傳。」兩人對編選《叢書》的看法不同。(詳見《顧廷龍文集》,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2年,頁453)陳福康也說:1941年6月鄭振鐸「所編《玄覽堂叢書》由上海精華印刷公司(商務印書館在滬印刷廠的化名)開始影印出版」(《鄭振鐸年譜》,頁317)。按《玄覽堂叢書》第一集選印多少種書,有不同的說法,《文集》說33種,〈國立中央圖書館復員以來工作述要(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乙文(刊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卷1期,頁69),則說31種。館長與館方的說法不同,是很奇怪的。陳福康《鄭振鐸年譜》說是34種,是第三種說法。筆者較支持沈津的說法:(《玄覽堂叢書》)初集31種,從版本來說,明刻本24種(《文集》寫26種),清初刻本1種,明抄本4種,抄本2種(見〈佇中樞以玄覽 頤情志于典墳──談《玄覽堂叢書》〉乙文),吳文祺〈回憶「孤島」時期的鄭振鐸同志〉乙文(刊載《鄭振鐸紀念集》),也說第一集31種。至於說《玄覽堂叢書》序文的作者,《文集》說是徐森玉,沈津已考證出是鄭振鐸,一些證據都說序文作者是鄭振鐸。
卷二頁928,《文集》載:《玄覽堂叢書》續集選21種附4種,於民國36年出版。〈國立中央圖書館復員以來工作述要(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乙文,進一步說:「三十六年八月,編印『玄覽堂叢書』第二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吳文祺前揭文(〈回憶「孤島」時期的鄭振鐸同志〉),也說是《續集》21種,同《文集》說法。沈津前揭文(〈佇中樞以玄覽 頤情志于典墳──談《玄覽堂叢書》〉乙文),說:《續集》收20種,計明刻本11種,明抄本3種,清初抄本暨舊抄本6種。所附書影:中華民國36年5月國立中央圖書館影印。《叢書》續集的種數有上述兩種說法。《國立中央圖書館六十年大事記(初稿)》載,第二集120冊,未注明種數,第一集有注明種數和冊數,惟說民國31年編印是錯的。第一集版權頁寫民國29年出版,實際上是30年出版。《叢書》第三集收12種,各家說法沒有爭議。
卷二頁941,《文集》略謂:蔣先生在民國18年的中華圖書館協會年會上,提一論文〈中國圖書分類之商榷〉,載《圖書館學季刊》1卷2期。二錯。一是論文名稱漏「問題」二字,正確題名為:中國圖書分類問題之商榷;二是卷期係3卷1、2期合刊,《文集》誤為1卷2期。(按,昌彼得〈蔣慰堂先生年表〉,中央圖書館閱覽組〈蔣復璁先生著述年表〉,題名和卷期,均錯)
〔卷五:雜論〕補正
卷五頁3,《文集》載〈一剎那中的決定〉乙文,是講抗戰期間中央圖書館請鄭振鐸、張壽鏞、何炳松、葉恭綽等人在上海、香港搜購珍本圖書的專文,宜歸入卷二圖書與圖書館類,不宜歸入卷五雜論。頁2載蔣先生在德國圖書館實習時,曾對其出版品和官書的呈繳工作,寫一報告,登載在浙江教育廳出版的月刊。未寫清楚篇名、刊名、卷期,讀者不便引用。按篇名為〈留德研究圖書館工作報告〉,刊名及卷期為:浙江教育行政周刊,3卷21期。至於〈一剎那中的決定〉乙文,缺失頗多,已在卷二頁926論及,此不贅述。又及,與〈一剎那中的決定〉乙文內容大同小異的文章,還有一篇〈涉險陷區訪「書」記〉乙文,載《中央月刊》2卷9期,《文集》未收,此文有「凡經九日之尋訪網羅,於是吳興張氏劉氏、金陵鄧氏、番禺沈氏諸家藏書,皆歸國有」,似有誇大不實之嫌。
卷五頁7-16,篇名〈石虎舊夢記〉,係蔣先生民國6年至19年住在北京(後改為北平)的回憶錄,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石虎」指北京西城西單牌樓北的石虎胡同,蔣先生曾在此前後住了八年。松坡圖書館第二館即設於此胡同內。此文主要內容之一,講的是民國5年、9年、11年、12年松坡圖書館的大事記,如:
民國5年蔡松坡將軍逝世後,新會(梁啟超)等在上海組織有松社。
民國9年新會自歐返國,想在北平(北京)從事文化運動,所以就將松社售去。
民國11年將(松社)圖書運至北平(北京)。
民國12年將這所房子(石虎胡同)改作松坡圖書館的第二分館,專藏外文書籍。第一館則在北海快雪堂,專藏中籍。
《文集》卷二頁620、621也提到民國9年、11年至13年松坡圖書館,共四年的大事記,如:
民國9年的冬天,梁任公先生與先百里叔(蔣百里)等從歐洲回來,採購了一萬餘冊的英、法、德文新書,想在北平(北京)的歐美同學會內辦一個讀書俱樂部,任公先生命百里叔主持,……。讀書俱樂部的編目是由北大同學陳國榘君負責,要我去幫寫一個時期的德文目片,大約有兩千餘張。
民國11年冬天,……百里叔也回到硤石,告知讀書俱樂部早已改組為松坡圖書館,……地點在北平(北京)石虎胡同七號,要籌備公開閱覽,因陳君離平(京)回粵,要我去接辦。
民國12年,蔣復璁擔任松坡圖書館的編輯。
民國13年,松坡圖書館開館了。
上列兩部分合併閱讀,仍遺漏松坡圖書館一些關鍵性的事件與年代,未能呈現該館完整的全貌,補充說明如下:
| 1. | 《文集》卷五頁8說梁啟超在上海組織松社,宜加民國7年。再補充說明:民國5年11月蔡鍔病故,12月梁啟超「為紀念蔡松坡計,發起創辦松坡圖書館」。(見《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世界書局,1958年,頁503) |
| 2. | 《文集》說松坡圖書館在民國13年開館,是幾月?第一館或第二館?按第二館在13年6月先開館,第一館是14年10月開館。 |
| 3. | 什麼時候決定分設第一、二館?按,係民國12年11月,松坡圖書館召開成立大會時決定的。 |
| 4. | 卷五頁12,載蹇季常是松坡圖書館總務主幹;宋益民、吳景熙合撰〈松坡圖書館始末〉(載《北圖通訊》1982年第3期)說蹇先生是主任幹事。前揭文〈石虎舊夢記〉頁14載丁文江到中央研究院後,松坡圖書館就此默默無聞了。按,丁文江民國23年5月到中央研究院。又按,民國38年春,松坡圖書館併入北平圖書館,其藏書就成為北平圖書館的一部分。計自成立到合併,歷時二十七年的歲月。有前揭宋、吳合撰乙文及梁啟超〈松坡圖書館記〉乙文,可供參考。 |
卷五頁11,載徐志摩〈石虎胡同七號〉乙詩,最後一段:「滿院只美蔭」,「蔭」誤為「陰」;「一斤,兩斤,杯底喝盡,滿面酒紅」,「杯底喝盡」與「滿面酒紅」之間,漏「滿懷酒歡」4字。
卷五頁15,《文集》載:梁啟超於「十六年一月十九日病故」,大錯,18年誤為16年。又載「我(胡適)老實說,我的哲學史是受著他(梁啟超)的先秦哲學思想大勢鳥瞰一篇影響的。」同樣是《文集》卷五頁26,又說:胡適認為自己的哲學史是受梁先生的〈先秦哲學思想大勢〉一文影響而作的。比較前後引梁啟超篇名,後者篇名最後漏「鳥瞰」二字。梁啟超的論述文章無此篇目,此篇目乃〈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之誤,此文曾連載於《新民叢報》。《文集》上說胡適的《中國哲學史》是受梁啟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影響,是對的。胡適的《四十自述》,有兩次提到此篇目。其中一次說:「《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也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知道《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胡適引梁啟超篇目也漏了篇名的第一字「論」。余秉權編《中國史學論文引得》和林慶彰、蔣秋華主編《晚清經學研究文獻目錄》,均收編此文。
卷五頁21,《文集》載:「今年(民國四十七年)十月四日,為先叔(蔣百里)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按,蔣百里逝世於民國27年11月4日,非10月4日。卷五頁55,《文集》〈先百里叔逝世追記〉乙文,蔣先生也是說蔣百里是10月4日逝世的,也是錯的。奇怪的是蔣先生在《蔣百里先生全集》第六輯編了一份〈先叔百里公年表〉寫「公(蔣百里)歿於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四日」。這是正確的。又,蔣百里先生逝世當晚吃的主食,《文集》卷五頁54,說是「晚上吃餃子」,《蔣百里先生全集》第六輯頁55說「晚飯時食麵一碗」,兩篇文章均由蔣先生撰稿,同一天晚上吃的主食不同。
卷五頁29,《文集》載〈徐志摩先生小傳〉乙文,文後注明出處:《傳記文學》1卷1期,民國51年。此文民國57年12月修訂後,收入《徐志摩全集》易篇名為〈徐志摩小傳〉,修訂的地方有十三處,如改「農報副刊編輯」為「晨報副刊編輯」;「十八年冬,聞新會(梁啟超)先生病亟」,改為「十七年冬,聞新會先生病亟」;「民國二十年三月,志摩自北平乘便機南歸」,改為「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志摩自北平乘便機南歸」;「子二,一早殤,一子在美經商」,改為「子二,一早殤,一子名積鍇在美經商」;「(徐志摩)作育人才,提攜後進,不遺餘力,沈從文氏即其一也」,刪「沈從文氏即其一也」8字,增「今日藝林,猶有不少健者,為志摩當年所陶鑄者也」20字。也訂正一些不重要的地方,如「小曼(陸小曼)實有志上進,而吾家不許之,卒成現在之局」,改為「小曼實有志上進,而吾家不之許,卒成現在之局」;「開智學堂」,改為「開智小學」等。
可惜的是仍有重要部分未增補,如徐志摩只寫生於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未寫生於1897年1月15日,夏曆1896年12月13日。《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也是寫生於1897年。編《文集》時,有修訂而未收,算是一大疏忽。
卷五頁46-47,篇名〈悼念袁同禮先生〉,《文集》收錄這篇文章,係刊登於民國54年2月10日《中央日報》副刊,距袁先生逝世不過三、四天,可能是據記憶寫成,所以內容頗多錯誤。如:
| 1. | 《文集》載,袁先生民國6年畢業於北大預科。按,袁先生民國2年考入北大預科英文甲班,肄業三年,民國5年畢業。 |
| 2. | 《文集》載,袁先生民國12年回國,任國立廣東大學圖書館館長,13年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按,袁先生是民國13年返國就任廣州嶺南大學圖書館館長。北京圖書館戚志芬1989年撰文,也是說廣東大學,1992年寫的文章,已改稱嶺南大學。張秀民發表在《北京圖書館館刊》的文章(1997年第3期),焦樹安發表在《國家圖書館學刊》的文章(2001年第2期),也是說嶺南大學。中國大陸出版的《圖書館學百科全書》,仍舊稱廣東大學圖書館。筆者認為嶺南大學最初由美國基督教會創辦,成立於西元1888年,歷史悠久,名聲較好,1922年譚卓垣曾任館長,後來又擔任過一次館長,有基礎才能編印《中文雜誌索引》兩巨冊。袁先生留學歸國,在此任館長,較有可能。廣東大學由時任大元帥的國父所首創,民國13年始由三所學校合併改組而成。袁先生在此大學服務,似無可能。袁先生是民國14年北上任北大圖書館館長,兼任目錄學教授,非民國13年。 |
| 3. | 《文集》又載:民國14年4月在北平成立了中華圖書館協會、選舉梁啟超任董事長、袁同禮任執行部長,這三件事前文已指出錯誤所在,此不贅述。 |
| 4. | 《文集》載,中華圖書館協會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時,有美國圖書館協會代表鮑士華博士致辭,《文集》卷二頁568,鮑士華提了兩次,一次附英文姓名:Dr. Arthur E. Bosewick,《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和嚴文郁的著作《中國圖書館發展史──自清末至抗戰勝利》都譯成鮑士偉。 |
| 5. |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有三次均誤為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 |
| 6. | 《文集》載:「民國十八年南北統一」,教科書都是寫南北統一是民國17年7月。 |
卷五頁109,《文集》載:「民國三十二年,中央圖書館借印故宮博物院藏四庫全書珍本初集之後,……」,民國23年誤為32年。按《珍本初集》始印於23年,24年出版竣事。
卷五頁111,《文集》載:「民國五十四年八月,……我因雲五先生的推薦,於是年九月由行政院聘任我為國立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可是《蔣復璁口述回憶錄》卻說:「我與故宮的這段因緣要感謝先總統的提拔,任命我為院長之事,完全由他決定,沒有任何人的介紹。」兩種不同的說法,不知孰是孰非。
卷五頁115,《文集》載:「(民國)十三年,(徐)志摩在北平西城中街成立了『新月社』」。按,《民國人物小傳》(傳記文學出版社,1975年)第一冊,亦稱民國13年徐志摩在北京成立了「新月社」。《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和《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這兩套筆者常用的工具書,都是寫民國12年成立「新月社」。另外,還有兩本筆者不常用的工具書:《大辭海.中國文學卷》、《中國現代社團辭典(1919-1949)》,也是寫1923年成立「新月社」。還有一部重要的小型資料彙編《徐志摩研究資料》(邵華強編,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乙書中,有〈徐志摩年譜簡編〉,其中載有1923年3月,新月社在北京成立。今年(2009)最新出版《徐志摩.新月社》(王一心、李伶伶著,陝西人民出版社),第一章徐志摩、胡適的聚餐會,第二章從「新月社」到「新月俱樂部」,都在討論「新月社」成立經過的種種說法,最後也是支持成立於1923年的看法。
同一頁又說:「抗戰期間我為中央圖書館採購了大批善本書,花了幾百萬元經費,……」。實際上,是花了三百二十萬元至三百五十萬元左右。
卷五頁116,《文集》載:「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古物遷臺」,按,古物遷臺,始於民國37年12月,故宮博物院320箱,中央博物院212箱,中央圖書館60箱。第二批才是民國38年1月。
餘論
拙文原題「蔣復璁先生研究述評」,為紀念蔣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而作,因篇幅過長,短期內無法完成,臨時改題先生《珍帚齋文集》讀後記。借到《文集》首先看自序,序文說:「積稿乃有百三十餘萬字。退休多暇,略加整理,分為五卷」。對成書經過未詳細交待,又無後記說明編輯和出版情形,最重要的是,要提哪些人協助校對。通常著作集或全集出版,都會附有作者的大事年表或著述目錄,《文集》兩者皆缺。筆者不禁懷疑,《文集》編輯時,先生已八十八歲高齡,可能全部自己校對嗎?如果是自己親自校對,就不會存在那麼多問題。那麼是誰參與校對?一個小組或一個團隊?開過幾次會?如有編委會,則正文後應有編後記。由於未透明化,產生疑點重重。筆者認為編輯此類著作集或全集,一定要組成一個編輯委員會,負責規劃、處理相關事宜。編委會的具體任務有下列六項工作:
1. 編輯著述目錄
編著作集或全集的第一步驟是編一份完整的著述年表。中央圖書館過去曾編過三次先生的著述年表和一次著作目錄,都不齊全,至少漏收十五篇以上。第一篇發表於1921年8月20日的《文學旬刊》11期,篇名是〈寂寞的城〉,是一篇譯文,著述年表和著作目錄,均未收。前提兩種年表、目錄所收第一篇是1926年8月發表於《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2卷1期的專題書目〈論語集目〉,兩篇發表的時間相差整整五年。其他漏收的還有:〈痛苦中之追憶〉(按,係追念蔣百里先生)、〈追念蔡(元培)先生〉、〈永生不是死──追念梅月涵先生〉、〈一個小學生記得的辛亥革命〉、〈蔣序〉(洪有豐著《圖書館學論文集》)、〈先叔百里公年表〉、〈蔣序〉(嚴文郁著《中國圖書館發展史──自清末至抗戰勝利》)、〈張君勱先生的追憶〉、〈敬悼毛子水先生〉、〈徐志摩先生軼事〉、〈蔣復璁院長序〉(李霖燦著《國寶赴美展覽日記》)等。
2. 提供著述目錄編選校勘
據著述目錄,複印兩份先生的著述文字,一份交先生供編選之用,一份供編委會校對之用,校對或校勘除了錯漏字之外,較重要的是引文部分,要找原書一一核對,一定會有錯字和漏字。像前文所提徐志摩〈石虎胡同七號〉乙詩,筆者就發現有多處是有疑問的,如《文集》寫「奈何在暴風時」,筆者查到的都是「奈何在暴雨時」。其他還有書名、篇名、刊名、卷期、地名、人名、機構和基金會名稱、年月日等,均須一一查核,將有疑問的,經整理後,向先生報告,由其定奪。
3. 討論正文的編排
編委會應統一規定文末必須注明原始出處,以利查考。目前《文集》所見,有部分注明原發表報刊的名稱、卷期和出版年、月、日。有部分未有注明出處,如〈臺灣藏書的鳥瞰〉文末空白,未注明原載《大陸雜誌》8卷2、3期,民國43年1、2月。有不少出處注明以前出版的選集,如《珍帚集》、《圖書與圖書館》,這是欠妥的。先生早期發表的文章,作者署名「慰」,或未署名,文末要加以說明。
4. 討論正文前後的輔文問題
包括正文前要加編輯或出版說明,是否加編例、照片、手跡等。正文後一定要有先生的大事年表或著述目錄,是否需要編書後索引呢?
5. 增編談論中央圖書館的專文
蔣先生的文章選定後,發現1933年(中央圖書館成立)至1949年之間,《文集》談論中央圖書館的專文,只有〈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之經過及現在進行概況〉、〈國立中央圖書館概況(民國三十二年)〉兩篇。核對兩文內容,發現有十三年的空窗期,補救的辦法是把《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卷1期的三篇文章當附錄編入。此三篇文章是:
(1) 1933年,〈呈教育部具報籌備經過及計劃〉。
(2) 1940年10月,〈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期間工作總報告〉。
(3) 1947年9月,〈國立中央圖書館復員以來工作述要〉。
加上卷五〈一剎那中的決定〉乙文,也可視為民國29、30年購書的專文。有了上述四篇文章,多多少少可補救中央圖書館歷史的空白。
6. 通讀與寫編後記
付印前或最後一校,編委會要找幾位對蔣先生生平著作甚為熟悉的人擔任通讀工作,每卷有一人通讀,最後一卷內容龐雜,不妨多人通讀。最後由編委會主持人和通讀人員,合寫一篇編後記。
以上是筆者初步想到,又可以做得到的,提供參考。
據說《文集》已售罄,建議出版增訂本,先就缺失、疏漏部分加以補正,再增加一些附錄。《文集》出版後,報刊上又陸續看到先生的著述文字,包括遺稿在內。據《國立中央圖書館同人著作目錄》所載,約有近二十筆,均可編選入增訂本。如果不再版,則可考慮出版全集,將《文集》尚未收入的四、五十篇文章,加以收錄。如不可更動原來版面的話,增加部分,編為續編或補編,估計可出版一冊或兩冊(增大事年表或著作目錄)。至盼計畫能早日實現,全集出版後,再著手寫一部「蔣復璁評傳」,這些工作完成後,庶幾可告慰先生在天之靈。
(拙文撰寫期間承吳穎萍小姐提供資料,謹此衷心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