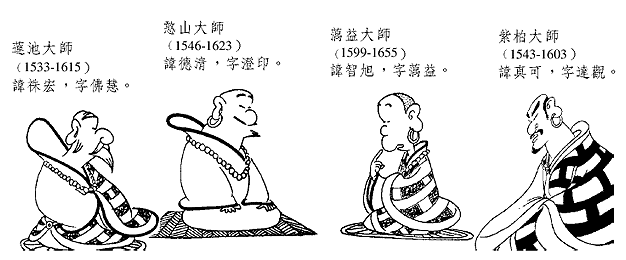/ 第 92 期 96 年 12 月 20 日出刊
大師相對論
五百年前,在晚明的中國我們不約而同的發了出世心, 在自己選擇的壇城中,奉獻「身」、「命」。 今日,當扣問的聲音再起時, 穿越時空之門,且讓我們在此相會。
穿越時空相會
從傳記裡,我們發現:四位大師(蓮池、紫柏、憨山、蕅益)見面的紀錄,曲指可數。以憨山大師為主,我們找到的紀錄資料主要是:
第一次:明神宗萬曆四年(1576),憨山大師三十一歲,在五臺山禪修。四十二歲的蓮池大師過訪,在禪淨雙修的體悟方面交換心得。
第二次:明神宗萬曆十四年(1586),憨山大師四十一歲,在山東牢山禪修。四十四歲的紫柏大師特意到訪,為刻方冊藏經之事,尋求憨山大師支持。
第三次: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蕅益大師廿四歲,決意出家後,三度夢見七十七歲的憨山大師(1623年逝,78歲),而從大師弟子雪嶺出家。
蕅益大師是四位中最晚出生的,從未與三位謀面;而另外三位大師雖然同時代,相聚的機會卻寥寥可數,甚至三位也不曾同聚。
今天,在我們不斷地扣問下,四位大師相應而來,將在此就相關的問題進行對談,讓讀者有機會親近大師風采,聆聽每一位大師對修行所抱持的不同角度與關懷。
今天的對談,我們分成四個主題。將從:出家動機,對世局的看法,己身奉持的修行法門,以及戒律的觀點等四個角度,分別來請教大師。
為什麼要出家?
重大的決定背後,往往有引人的故事。四位大師發心出家時,佛教並不興隆,但為何決定出家,請您們各自談一談出家的因緣,好嗎?
蓮池:袾宏俗姓沈氏,沈家在杭州還算是個望族。因此,家庭環境還不錯,自小便接受儒家正統教育的訓練,以待科考,希能一舉成名,顯耀親族。
決志薙髮出家,是在母親往生之後,但一腳跨入佛教修行之門,絕非衝動的決定,而是一連串因緣變化和合而有的結果。
出家前,從遊講藝,皆已回歸佛理,棲心於淨土。家裡戒殺生,以素齋祭祀,也有段時日了,常有「人命過隙,浮生幾何」之嘆!等到自己的兒子、前妻死亡,接著父母相繼過世,才親身體驗到生離死別,心中深深烙上了「人生無常」。
因此,母歿時,感念親恩罔極,想,該是報答親恩的時候了,便定了出家之志!就在那年的除夕夜,妻子湯氏端茶給我時,杯子突然墜地破裂,若是他人,可能會認為這是不吉之兆,但自己反而有所領悟,笑著說:「因緣無不散之理!」
過完年後,便與湯氏辭別:「恩愛不常,生死莫能替代,就此拜別,您自己保重。」
問:大師相當著名的《七筆勾》,好像就是在這個時候寫的。
蓮池:慚愧慚愧,《七筆勾》的內容好像有些感傷,不過,當時的心情確實就是如此。
問:憨山大師好像在年紀更小的時候,就對生死問題產生疑惑,是相當的早熟。
憨山:一切也是因緣的湊泊。七歲時,面對叔父死亡、嬸母得子後,心中便縈繞著死去生來的問題,不得釋解,不斷地追究:人的生命本質為何?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所以,有人笑說,那是我「第一次心靈上的危機」。
十九歲時,朋友們應考科舉皆傳捷訊,便有人勸我應試。此時的自己面臨了儒、佛身分的抉擇:要做儒生應科舉?還是選擇出家修道?
正好雲谷禪師(1500-1579)知道這件事,擔心我有去佛入儒之意,便對我大力開示「出世參禪,悟明心地之妙。」又勸讀中峰明本禪師(1263-1323)的《廣錄》。書還沒讀完,就深受感動,讚嘆地說:「此予心之所悅也!」便毅然決定這輩子就做出世事,不去參加科舉了!
問:在憨山大師的描述裡,紫柏大師您是個年齡愈長,志向益為廣大,羨慕俠義之行的年輕人。給別人的印象就是個慷慨激昂、不拘泥常情、欣羨遊俠的血性漢子。您也描述當年的自己是:「屠狗雄心未易消!」怎會選擇出家呢?
紫柏:真是慚愧。我本是個「殺豬屠狗之夫,唯知飲酒噉肉,恃醉使氣而已。」哪裡知道什麼佛法?
話說那天,在吳門楓橋,我出遊避雨,偶然遇到明覺法師,天色既晚,他便邀我回寺裡休息。
晚課時,聞寺僧誦《大懺悔文》中八十八佛名時,深受感動,內心非常暢快愉悅。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向明覺法師表白:「吾兩人有大寶,何以污在此中耶?」便請求明覺法師為我剃度。「道人一傘之接,雨漸而為甘露。」總之,自己的出家是相當豪邁灑脫,當下立即決定的行為。
這乍看是個衝動的決定,但出家為僧還是與自身性情相應。從小,便欣羨遊俠之行,俠士是不會只關心自己的利害,而是將心力轉注於他人身上,關懷需要幫助的人。這樣的特質與佛教的發願、回向,要濟助別人,不獨佔功德,樂與眾生分享是不謀而合的。
但是,身為俠者,若不能時時省察、反思、懺悔自己的所做所為,反而會有由「俠」轉「霸」的偏頗。
因此,一「聞僧夜誦八十八佛名」時,會「心大快悅」,隔天就馬上出家,還是有其緣由。
問:所以,紫柏大師出家的決定,真可說是立即且戲劇性的過程。這不同憨山大師於年幼見叔父死、嬸母得子,心中一直縈繞著死去生來,而有探究生死大事的初衷。
亦即並非動心於「悟明心地之妙」,而是聽聞《大懺悔文》後,直接進入「懺悔」、「發願」、「回向」,受到宗教情意的感動而發心出家的。
紫柏:想想,才認識一天,就向明覺法師要求出家,不顧什麼「才初相識」,自己也算是個「性情中人」吧。
問:蕅益大師還沒出家前是位儒生,以傳承千古儒學自任,以「儒學傳燈者」自居,誓滅釋老,有著「捨我其誰」的使命感特質。從謗佛到學佛,甚至出家的關鍵是什麼呢?
蕅益:智旭少時毀謗三寶,罪滿虛空,在讀了祩宏前輩的《自知錄序》及《竹窗隨筆》後,方知自己的無知。
《竹窗隨筆》是前輩對「儒釋和會」、「出家學道」等論題所作的辨析、澄清,而這些觀點令我折服,也改變了後學的闢佛觀。
至於發出世心的關鍵點,是在家父往生時,聽聞到地藏菩薩的本願:地藏菩薩前世為婆羅門女時,救母脫離地獄的因緣,讓她看到地獄眾生的苦難,而發弘願:「願我盡未來劫,應有罪苦眾生,廣設方便,使令解脫。」
地藏王菩薩的修道因緣是從「孝」發心,推至廣度一切眾生,這激發了自己想離俗染、報親恩。因此,便生起出世心,決意出家修道。
對世局的看法
晚明時期,世局混亂。身為一個出家人,要在混亂的局勢中自處,也要關心社會、國家。不知四位大師對於當時世局的看法如何?是回應:「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呢?或是感嘆「國土危脆」呢?
蓮池:袾宏生不逢時,不能生於與佛同世的正法時期;曾在〈彌陀疏鈔〉提過:「袾宏末法下凡,窮陬晚學,罔通玄理,素鄙空談。畫餅何益饑腸,燕石難誣賈目。」自問尚且不能明事,哪來的智慧理論世局?
知道自己淺劣有限,對「言過其行」深感可恥,所以,我不「空談」。也曾在〈畫像自贊〉中描述自己是「瘦若枯柴,衰如落葉,獃比盲龜,拙同跛鱉。無道可尊,無法可說。」因此,也只能奉勸大家:「但念阿彌陀佛!」
憨山:蓮池老大哥,您太謙虛了!剛出家時,德清也是「只憂自己道業成就否?」
但隨著出家年月增長,也憂心百姓、社會、國家!流放到雷州時,見到當地慘況,德清曾在寫給雪浪法師的信裡提到:「值歲饑異常,米穀湧貴,民不聊生。從去秋七月,至今不雨,野無農夫,戶有盜賊,而雷陽尤甚。……今復瘴癘大作,死傷過半,道路枕藉,悲慘徹心。」
目睹雷州百姓之苦,身在中國大乘佛教,德清不禁要從「自了生死觀」擴大為「人間菩薩觀」。出世法是不離世間的!
所以,流放從軍時,曾在〈軍中吟〉自白心聲:
「……從軍原不為封侯,身經赫日如爐冶,傲骨而今鍊以柔。」「緇衣脫卻換戎裝,始信隨緣是道場;縱使炎天如烈火,難銷冰雪冷心腸。」
自己從軍的原意,本就不是為了求官祿討生活,而是將之當成修行過程裡的磨鍊。一切磨難皆作洪爐冶鐵,只求能將一身傲骨化成繞指柔。因此,常要求自己:隨緣即是道場,處處自在。
紫柏:憨山兄,您說得即是!看看我們所處的萬曆年代,並非太平盛世,而是昏君當政,吏治敗壞,黨爭滋蔓不息,賦稅繁重,民變、兵變四起的時代。
這樣一個風雨飄搖、剝削的時代,達觀不忍坐視這些貪暴無能,握著生殺大權,榨取生民血汗的君臣為所欲為,於是提出了「民為國本」的呼籲:虐殺百姓,無異於滅君。混亂的世局,身奉出世間法的佛教徒,定要挺身而出,不然世變難以終止。
當年身陷獄中時,審判官王之禎問我:「你是個出家人,留在山中修行是本分。不在深山修行,為何要到京城結交士大夫,干預公事?」達觀的回答是:「我是為了刻《方冊藏經》,修《高僧傳》,編《續傳燈錄》,還有營救憨山法師等,才來京中暫住,並不是為了自己而戀戀紅塵。」
問:這應該就是紫柏大師您三大負欠的感慨:「老憨不歸,是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您關切民間疾苦,也以佛門慧命為念,這三大負欠沒有一樣是為了您自己!
至於蕅益大師,史料上很少提到您參與國家社會的運動,這一點,您的想法是什麼?
蕅益:智旭所處的年代,是萬曆廿七年(1599)至順治十二年(1655),那是十六、十七世紀交替的中國。也是不平安的時代。
政治紛擾,流賊四起,接著清兵入關,是一個改朝換代的亂世。天災、人禍相逼而來:旱災、蝗害、河堤潰決不斷,連年饑荒、兵變,處此亂世,民眾淒楚無依,流離困頓,智旭只能慨歎「孤臣無力可回天」!
雖然如此,既出家為僧,面對這樣的社會,自己也有宗教責任。但並非選擇直接入世,參與救度;而是以宗教行持來回應時代,以滿懷的悲心、同情心傾注於一切眾生。所以,我常常為國家、社會與百姓禮懺、祈願。
智旭感嘆自身障重,生不逢時,目睹時艱,「斗米幾及千錢」,而嘆民生之苦;面對「病死日以千計」,而驚訝眾生業報之深。這一切都是眾生共同所感的惡緣,共同感受的苦報。雖然佛法說這分苦報亦是幻相一場,但是,我怎能坐視這場劫難呢?
雖有滿腔熱血,但獨木難撐大局,只能藉著精勤行持的力量,來改造自己、法運及世運。竭盡己力,代眾生發願、祈求疾疫消除,刀兵偃息,風雨順時,穀物豐稔。內心祈望:百姓常享太平豐樂,不遭離苦饑荒;正法能長久住世,眾生能離苦得樂。
問:憨山大師曾以「性剛猛精進,律身至嚴。」描述紫柏大師;後世以「苦急嚴峻」形容蕅益大師。二位大師的個性或有相似之處,為什麼您們二人所選擇的方式如此不同?
蕅益:智旭曾受益於紫柏前輩,在點完前輩的文集後,後學曾心有戚戚焉寫下:「今觀其法語,精悍決裂,猶足令頑夫廉,懦夫立。柔情媚骨,不覺冰消瓦解。」前輩的剛猛之氣是向外發,直接投入濟世救民的菩薩道,如同人間的俠僧。智旭則不然,我將自己滿腔的熱情,內化於一生的宗教行持。除了虔敬發願,精勤地禮懺、持名、持咒,甚至以血書、燃臂、燃頂來表達自己虔敬發願之心。
這一生修行的色彩,願用一偈來表達:「照我忠義膽,浴我法臣魂;九死心不悔,塵劫願猶存。」
參禪?念佛?
出家人對自己的修行法門,常會選擇「一門深入」。參禪和念佛,一直是中土佛教修行的重要法門。四位大師對於自己修行法門的選擇,是偏重參禪呢?還是偏重念佛?
蓮池:祩宏一再表明心志,平生所務在於「南無阿彌陀佛」六字。一如自己在〈勸修淨土代言〉的表達:「袾宏下劣凡夫,安分守愚,平生所務,惟是南無阿彌陀佛六字。」
只是,袾宏說的:「往生淨土,願見彌陀;不礙唯心,何妨自性。」常被人誤解為:念佛即是念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所以不須假借他方,當下即可「心淨則國土淨」。如此,依「唯心淨土」,再發展成「心淨則國土淨」,很有可能就會走上「人間淨土」的路徑。這並非祩宏理解「不礙唯心,何妨自性」的本意。
換言之,祩宏不認同「自性彌陀,唯心淨土」即是「心淨土淨」,就不需往生西方的論點。
我所理解的「自性彌陀,唯心淨土。」其路徑是與「往生西方,願見彌陀」結合。唯有西方淨土最為殊勝,與其來娑婆世界為僧,不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為僧,因為西方淨土遠勝於此啊!
自己非常清楚:此世與彼世,是絕然地二。此岸是污穢、痛苦;彼岸是極樂、清淨。縱使凡夫眾生已初發菩提心,仍如弱羽只可棲息枝頭,難以自在飛翔。因此,才會勸人以西方極樂世界為弱羽纏枝之處,方是穩當。
憨山:老大哥說得是。至於德清對修行的體會,則必須從自己選擇出家的因緣來探討。
我本是一介儒生,是受到雲谷禪師的開示,和中峰禪師《廣錄》的影響,才決定做出世事,此生當了生脫死,明心見性。
初入佛門之時,經驗見識皆淺,不知佛法的廣大,以為遁隱山嶺、寂守枯禪就是修行。後來親近大乘經教,方知「無一事而非佛事,以不捨眾生,乃見佛慈之廣大;不棄一塵一毛,方識法界之甚深。」(《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二十四.麗江木六公奉佛記》)
原一心一意只顧追求個人的生死大事,直到接觸華嚴等大乘經教後,自己才發了迴小向大之心,這是德清學道歷程的一大轉折。
自此,形成了德清一生對修行的信念:「出世法不離世間法」。我曾在〈示妙湛座主〉中表達過這個想法:「向日用現前境界,生死岸頭一一透過。即此日用不離一法,不住一法,處處不輕放過,便是真切功夫。
即此目前一切聲色、逆順、愛憎境界,一一透得過,便是真實悟門。即此悟處頭頭法法,便是真實佛法。」
自己常憂心:「道在日用而不知,道在目前而不見;以知日用而不知道,見目前而不見道。」因此,學道之人「不必向外別求玄妙。茍於日用一切境界,不被所瞞,從著衣喫飯處一眼看破,便是真實向上功夫。有志於道者,當從日用中做。」
強調「道在於日用中」,處理好現前境界,就是「今雖荷戈行伍,何莫非佛事。」
紫柏:憨山兄說得妙!我倆對修行所見不遠。達觀剃染出家後,也覺得出家人本分之一,就是照顧好自己的生死大事,要精進勇猛,律己謹嚴,克盡僧人本分,依佛制而行。
所以,在受完具足戒,也閉關了三年之後,還是對家師明覺法師說:「吾當去行腳諸方,歷參知識,究明大事也。」(《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廿七.徑山達觀可禪師塔銘》)
不過,達觀和憨山兄迂迴曲折的修道歷程仍有不同。
從初發出家的動機開始,自己便已直入大乘利他精神的修道生涯。除四處參訪善知識外,還深信持誦毗舍浮佛偈的功德—「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深信:前半偈,能有效幫助常人捨棄對身見的執著。這半偈,能讀而誦,誦而思,思而明,明而達之後,惡源能枯或不枯,罪藪能空或不空,個人自然就會知道了。
憨山兄,您還記得嗎?有一次,您問我持否?我回答說:「吾持二十餘年,已熟句半。若熟兩句,吾於生死無慮矣!」(《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廿七.徑山達觀可禪師塔銘》)
此話果真在後來達觀蒙受冤獄時應驗,當時確實能不被自己身形所累,從容坐化而去。
蕅益:聽三位前輩談自己對修行的觀點或法門,後學亦有所感,也願意談談自己的淺見、淺行。
初出家時,智旭志在宗乘,「苦參力究」的參禪。雖不敢起增上慢,自謂到家,但下手工夫還頗為得力,便志高意滿,認為憑自力就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解脫。
但在生了一場瀕死大病之後,才知平日用功得力處,分毫用不著,此時才一心一意歸心淨土。這是自己由參禪轉淨土之機。此時雖一意西歸,卻仍不捨本參,仍屬有禪有淨之列。
等到拜訪了無異博山禪師(1575∼1630年),熟知末代禪病—空腹高心,鳥空鼠寂—之後,便索性棄禪修淨。智旭捨禪專修淨土,正是為了對治末代禪病。
因此,三十歲所寫的《梵室偶談》仍認為:參禪者想往生西方,不一定要改成念佛。只要具足「信」、「願」,仍可往生西方。此時自己還是主張「念佛參禪併行論」。
可是後來看到禪者胡扯公案,智旭不得不轉向更重視念佛。待四十九歲著《阿彌陀經要解》時,已不信「參究念佛」了!
相對自己與祩宏前輩的差異是:智旭後來抑禪揚淨,並不贊同祩宏前輩的「參究念佛論」,欲建立淨土宗獨立的姿態;而祩宏前輩始終主張參究念佛,認為禪淨可以雙修。
問:好像二位大師在所謂的「理一心」「事一心」,或名「事持」「理持」,看法也不同,可否請二位說明?
蓮池:可能是我主張參究念佛,所以「事一心」約指持名念佛,字字分明,相續不斷;而「理一心」即由參究念佛得之,聞佛名號不只憶念,亦能反觀,而體察究審,極其根源,於自本心而契合。
因此,以「憶念無間」為事持;「體究無間」是理持。所謂體究無間是「體察究審,獲自本心」之義,又名「達摩直指禪」,倡導禪、淨二宗的融合一致。
蕅益:智旭後來不再贊同參究念佛,因此對事、理一心的詮釋,當是有別於前輩。不論是「理一心」或「事一心」,皆指憶持阿彌陀佛,不忘其名號。差別在知此佛是己心具足,或不知心具。
簡單地說,所謂「事持者」,即尚未明達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理,但信西方阿彌陀佛,決志願求往生。「理持者」,即信西方阿彌陀佛就是我心本具、我心所造,而以自心所具所造的名號作為繫心的所緣,暫不忘捨。
因此,「事一心」、「理一心」皆指「憶持不忘」,只在「知心具」或「不知心具」的差別。
強調一點:雖然智旭不認同「參究念佛」,卻沒排斥「彌勒信仰」。可以先往生西方極樂,待龍華初會彌勒成佛時,我發願當影響眾,協助彌勒度眾生。同時也學地藏菩薩的發願,「眾生度盡,方證涅槃」。
因此,智旭的彌陀信仰是參雜地藏、彌勒信仰的。
戒律與清規有何不同?
持戒是佛陀對出家人的基本要求,出家人也以戒自律。只是,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國之後,歷來祖師面對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政治生態,發展出特有的中國佛教叢林的團體生活型態。
因此,從百丈清規到蓮池大師設立團體共住規約,甚至在其所註解的沙彌律儀中,對於沙彌律儀的要求,都摻雜了中國儒家的思想。清規與戒律,對於出家眾個人或僧團,與原本佛陀所制的戒律,有什麼不同呢?
蕅益:提到這個議題,智旭有許多的感觸和看法,後學就先發言了!
出家後,自己的心思一直留在「宗乘」,但每至功夫將得力時,必被障緣侵惱,常想到佛滅度時,交待弟子要「以戒為師」。事實上,廿五歲在徑山坐禪時,自己還不知受戒一事,何為如法,何為不如法,都不清楚。
就在那年的臘月初八,杭州雲棲寺有學戒科,便從天台山躡冰冒雪,來到浙江雲棲寺受具足戒。這是在出家後,以戒為基,開啟了此生以復興戒律為志業的緣由。
問:大師廿七歲,第一次閱律藏,三十歲第二次,三十二歲第三次,對於佛陀所制的戒律,是下過苦功的。但大師於三十二歲第一次講戒律後,竟中斷了十餘年,直至五十二歲才又重新講戒。
蕅益:關於此事,自己也曾嘆道:「從此十三四年,無有問者。……毗尼之學。真不啻滯貨矣。」(《靈峰宗論卷六之四.重治毗尼事義集要自序》)
興復戒法,除講戒之外,註釋律本也是自己用心之處,如《重治毘尼事義集要》、《梵網經合註》……等。三十二歲,我見戒法傳到明末,已是「但見聞諸律堂,亦並無一處如法者。」因此,曾力求「五比丘如法共住,以令正法重興。」智旭曾與惺谷道壽法師、歸一受籌法師、雲航智楫法師和璧如廣鎬法師結盟。可惜隔年,惺谷法師與璧如法師相繼而逝;五年後,歸一法師背盟而去。因緣皆不具足,「五比丘如法共住」的想法,功虧一簣。
之後,自己這復興戒律之志,遂成槁木死灰。不禁感嘆道:「予運無數苦思,發無數弘願,用無數心力,不能使五比丘如法同住,此天定也!」(靈峰宗論卷六之一.退戒緣起並囑語)
正法衰微,已如游絲,誰來將此一線傳繫?我對自己持戒、弘戒之事仍不甚滿意。半世以來,自己彷若一盞「孤燈」,但還是不願放棄,仍不遺餘力地講述戒律的重要性及地位。
問:與大師同時代弘律的蓮池大師、見月讀體律師二位相較,發現蕅益大師您較強調個人持戒,而他們二人則是以遵守僧團清規為主。為何有這樣的差異?
蕅益:戒律,是佛陀時代制訂,留傳下來的;清規是適應中國佛教之需而發展的,多是叢林組織規程及寺眾日常生活的規則。
祩宏前輩長智旭六十六歲,前輩所處年代,朝廷禁止設戒壇傳戒。前輩為了振頹綱,又不願違法,所以令僧眾半月半月誦戒,及布薩羯磨。此外,又設清規安眾,令各執有所司,重整寺院組織及生活細行,讓僧眾知所依止。
所以,憨山兄曾讚嘆祩宏前輩時代的雲棲僧團是「古今叢林,未有如今日之清肅者。」
見月讀體律師則小智旭三歲,也是明代偉大的律師。較晚期的弘一法師曾讚歎他:「儒者說:『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我於師(見月)亦云然。」
見月律師出家、受戒、閱律藏,後來隨寂光三昧法師接管寶華山。其於三十九歲時,參與寶華山的戒期。戒期結束後,三昧和尚為其他沙彌受比丘戒。見月律師認為不合律制,挺身勸諫,得到三昧寂光法師的稱讚:「我老人戒幢,今得見月,方堪扶樹耳。」
反思我自己,只能寫寫文章,說:「只見律制衰微,當時所行不合佛制。」卻難以如見月律師為維持律制,而有力爭到底之行;亦只能感嘆地說:「僻處深山,以作傳火之計。」
見月律師四十四歲時,寂光三昧法師病危,將寶華山交給他負責。他上任後第一件事,即是「宜速立規條,先革弊端。」於是與寶華山住眾立十事為約,使寶華山能淡薄隨時,清淨傳戒。
祩宏前輩、見月律師以僧團為單位,透過中國化佛教的清規來領眾、檢肅僧眾,令住眾能安住律儀,令僧團能清淨住持正法城。
而智旭一生常是自己一人或與少數盟友、道友、弟子修學,未能形成一個僧團,沒有與大眾共修、共學的機緣。較屬於規範個人戒行的戒律,而非以清規為復興對象,這或許與我個性孤峻有關吧!不適宜過大眾共修、共學的叢林生活,而以獨修、獨學的生活為主。一生中,較有來往的盟友、道友,也不過八位而已。
蓮池:蕅益小弟,您辛苦了!對於您致力復興戒律並力行之,袾宏由衷感佩。
其實,初出家時,本想一人獨自修行。但隨之而來的僧眾,或要切磋問道,或共修共住,雲棲寺才漸成一方叢林。大家為修行共聚一處,本是美事一樁,袾宏也難以拒絕,所以才會說,這是「事事皆出勢所迫,而後動作。」
立清規,讓雲棲寺逐漸蔚為一方叢林,且力行古道,禪淨並行,因此僧規井然有序。雲棲寺僧眾的素質提昇了,無賴亦不敢濫竽充數,參雜其間,雲棲寺才能贏得佛教界與社會大眾的認同。
不過,自己也明白佛陀時代所制訂的戒律,與為規範僧眾所立的清規之間,已有很大的不同,但也只能隨情勢所為了!
憨山:對於這個議題,是德清行事比較不及的部分,所以不敢多言,謹聽各位教誨。
紫柏:出家四十餘年,平日過的是:睡時脅不至席;過午不食;常露坐不避風霜。雖如此,但身為比丘,不能完全遵守佛制,也不是很滿意自己。
不過,蕅益小弟您盡心盡力在晚明恢復佛制,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難怪會有「孤燈之嘆」!達觀是深感佩服!